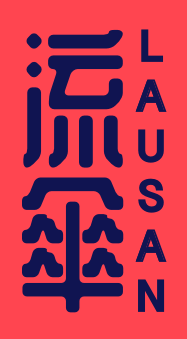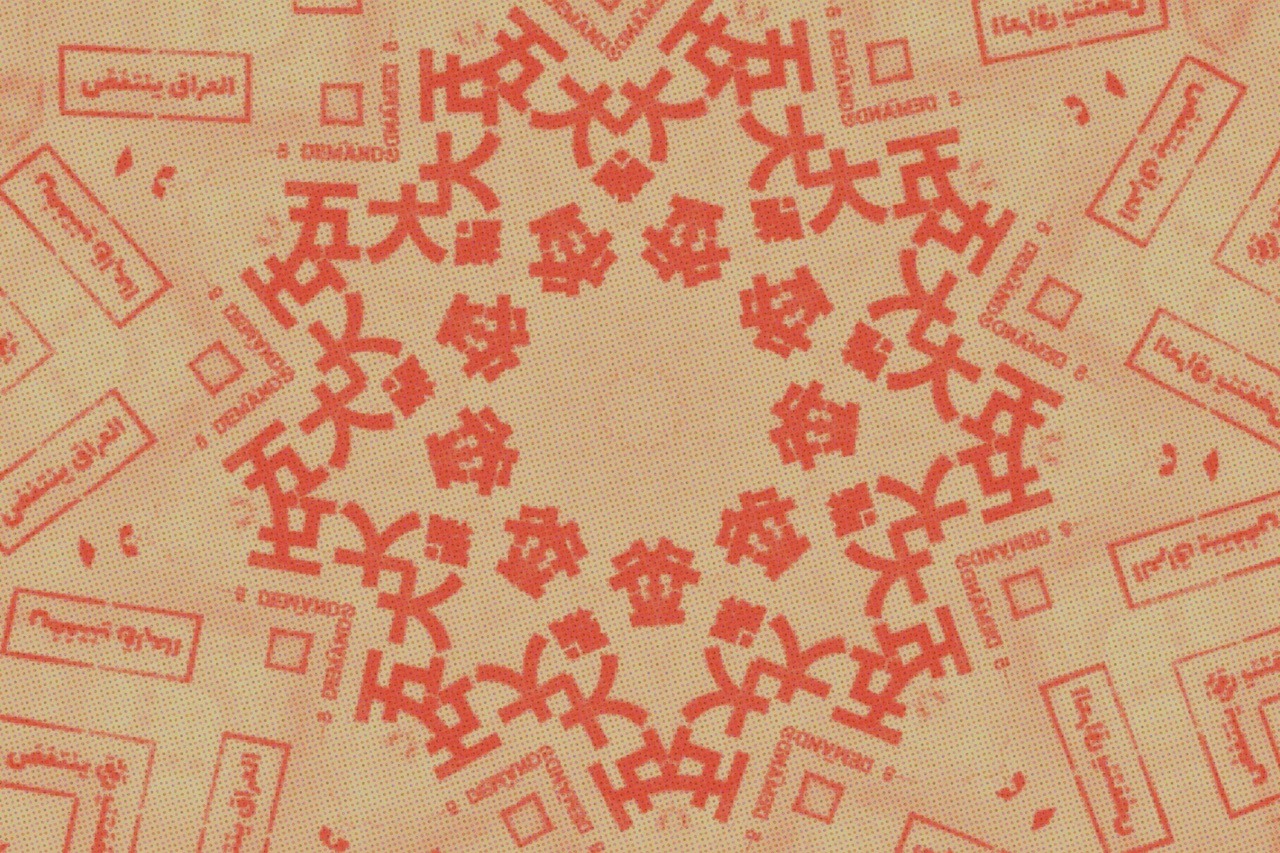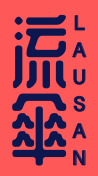編按:2019年,香港和黎巴嫩同時發生的兩場起義激發兩地的行動者、組織者和作家參與並思考彼此的鬥爭。近日,流傘與黎巴嫩行動者、作家和學者Elia J. Ayoub討論了持續的抗議活動、兩地鬥爭之間的呼應和跨國團結的可能。
英文原文見此。詳情請聯絡流傘義務翻譯團隊。
譯者:Paradoxite
「人民要政權垮台」:鬥爭中的黎巴嫩
流傘:能不能簡單跟我們說說黎巴嫩的抗議是怎麼開始的?
Elia J. Ayoub (EJA):黎巴嫩存在一種教派主義制度,基本上是教派精英之間的分權協議。通常舉的例子是,黎巴嫩總統必須是馬龍派基督教徒(Maronite Christian),總理必須是遜尼派穆斯林(Sunni Muslim),議長必須是什葉派穆斯林(Shia Muslim)。這意味著,與敘利亞、利比亞、埃及、突尼斯甚至香港不同,黎巴嫩沒有佔主導地位的權力象徵,沒有阿薩德(Assad)、卡扎菲(Gaddafi)、穆巴拉克/塞西(Mubarak/Sisi)或本·阿里(Ben Ali),也沒有習近平和中國共產黨。
這正意味著黎巴嫩既穩定又脆弱的局勢。儘管衝突一直存在,但大多數情況下這個國家都能經受住教派紛爭的洗禮。況且人們從沒有一個明確的目標對象來推翻。因此當2011年埃及、敘利亞、利比亞、突尼斯等國人呼籲推翻本國政權時,黎巴嫩只有少數人提出了同樣的要求。

2015年「你爛臭了」(“You Stink”)抗議中曾有過一個短暫的動員期。這個抗議的導火綫是一個大型堆田區被關,垃圾堆積到了貝魯特和黎巴嫩山(Mount Lebanon)的街道上。更廣泛地說,這也是一場反對政治體制腐敗的抗議。
但我們真正登場是在2019年。當時多年來的廣泛腐敗和災難性的經濟政策導致了嚴重而持續的金融危機,又偏逢鄰國敘利亞內戰。終於,十月十七日,成千上萬的抗議者鼓起勇氣高呼「人民要政權垮台。」運動持續至今不絕。
香港和黎巴嫩並觀:時間的焦慮和被消失的恐懼
流傘:最初是什麼促使你思考黎巴嫩的十月起義和香港的反送中抗議之間的聯繫的?
EJA:抗議開始後,我們立刻就看到香港的抗議策略被借鑒到黎巴嫩。抗議者開始用大功率激光和刺眼的燈光來迷惑安全部隊,這是他們以前從沒嘗試過的。我們還根據來自香港的戰術學習了怎麼對付催淚彈。
奇怪的是,黎巴嫩和香港之間的相似點其實不是什麼新鮮事。內戰之前和期間(1975-1990年),拿貝魯特與香港或河內作比較並非聞所未聞。有時有人說,黎巴嫩面臨著非香港即河內的選擇。對當時的一些人來說,作為殖民前哨基地的香港是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的代名詞,而河內則代表著社會主義和反帝國主義。雖然這種二元對立總是過於簡單化,但它實際上為黎巴嫩的一部分黎巴嫩裔和巴勒斯坦裔左派開創了與越南的鬥爭串聯的空間。

2019年的抗議給了我一個藉口去重新審視這個二元對立中的一些動態,並嘗試解構其中的矛盾。比如說,目前河內已經變成了全球資本主義的主要參與者,而香港抗議者則通過比如佔領機場對資本造成直接的威脅和傷害。如今黎巴嫩那為數不多的曾用香港/河內作比喻的左派,對此會怎麼說呢?我猜他們能說的不多,因為二元論所創造的修辭模式(rhetorical schema)往往比它們被創造之初的所謂目的更持久。簡單化的二元論會經久不散。
在我看來,香港和黎巴嫩之間更有趣的類比是,它們在「時間上」(“temporally”)都是那麼地「脆弱」。在和流傘的一位成員交談時,你這位同事向我介紹了Ackbar Abbas的《香港:文化和失踪政治》一書,我不由得想到,「失踪」這個詞既代表了香港經驗,也代表了黎巴嫩經驗。
我們所認識的一切不是已經消失,就是正在消失中。我們聽著貝魯特電車和黎巴嫩火車的故事長大,但這些都在戰爭中被摧毀了。我們親眼目睹公共空間被抹除,古老的森林被夷平,海岸線被私有化得面目全非。我們的城市仍然佈滿彈孔。我們的國家擁有世界上一些最古老的城市──比布魯斯(譯註:現稱朱拜勒)、蒂爾、貝魯特、西頓、的黎波里──然而我們卻陷在最多只有幾十年歷史的暴力循環之中。
內戰之前和期間,作為殖民前哨基地的香港是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的代名詞,而河內則代表著社會主義和反帝國主義。這種二元對立總是過於簡單化。
Abbas在1997年撰文在香港語境下反思了這個主題,他的書促使我思考2047年(譯註:「一國兩制」承諾)的「到期日」對香港人意味著什麼。如果2047年已經在2020年提前到來,是否當下和未來之間的界限模糊了?在「時不我待」的心態下,人們會如何實地應對這個狀況?我們如何調動這種對消失的恐懼來維持一場運動,去守護那些正在被消失的事物?1
我認為,維持黎巴嫩運動的一個關鍵是藉鑑其他地方──比如香港──的運動。與香港不同的是,我們沒有一個可以看作「到期日」的具體未來日期。相反,我們的情況是過去仍然困擾著現在,這一點我相信世界各地的行動者都會有同感。在我們這裡,內戰的「未完成時」是壓倒性的。目前參戰的大多數軍閥仍在掌權,我們的「被失踪者」仍無踪跡,以色列和阿薩德政權的威脅也從未遠去。
黎巴嫩和香港之間最後一個相似之處是,移民和難民還是繼續被排除在被看作我們「自己人」的抗議之外。移民和難民基本上只能旁觀革命抗議,因為積極參與的風險實在太大了。主流運動中很少提及巴勒斯坦人和敘利亞人的鬥爭。
我們仍有待看到相當比例的抗議者要求廢除帶種族主義的卡法拉(Kafala)「擔保」制:該制度將移民家政工人的法律地位與其雇主掛鉤,從而主導了他們的生活。諸如「東道主/難民社區」、「黎巴嫩籍/非黎巴嫩籍公民」等二元論不斷被當權者和普通公民強化,這與黎巴嫩歷史上某些時期的包容性(inclusion)動態(最主要的是產生了黎巴嫩裔亞美尼亞人)形成鮮明對比。
「每個國家都要革命」
流傘:我本人很受推特上被廣泛分享、黎巴嫩女權行動者喊出的「每個國家都要革命」口號的鼓舞。你知道這個口號是怎麼來的嗎?你覺得為什麼正正是女權主義者撰寫並喊出了這句口號?
EJA:我認為,女權主義者比其他群體看得更清,因為她們本身就生活在黎巴嫩背景下的邊緣空間(liminal spaces)。為了生存,她們可以在日常生活中操演(譯註:perform,或指身份政治研究中的「操演性」(performativity)概念)出基於公民權的身份。但她們對全球和本土的父權制結構的抵抗擴大了團結的可能性。對她們來說,地方的就是全球的(the local is the global)。因此,女權主義者比其他群體,包括更傳統的左派,更有能力踐行一種能夠解決多元身份壓迫(intersectional forms of oppression)的政治。
黎巴嫩有太多女權主義行動者在爭取婦女解放的鬥爭中犧牲了。在這裡我想一提Nadyn Jouny:她為了保住自己孩子的監護權與黎巴嫩宗教法庭進行了鬥爭。 Nadyn是2015年運動的組織者之一,是一位非常優秀的女性,一個心地善良的人。就在2019年起義開始前幾天,她死於車禍。她到死亡之際都在戰鬥。我知道,那群女權行動者在高呼「每個國家都要革命」時心裡想著的是她。
這首女權頌歌之所以那麼重要,是因為它迫使我們擺脫黎巴嫩歷史的循環。我的意思是,黎巴嫩歷史的特點是以十五年左右為周期的起伏。 1943年,黎巴嫩宣布獨立;十五年後,1958年衝突爆發。 1975年,內戰開始;十五年後,內戰結束。
2005年,總理Rafik Hariri被暗殺,開啟了由「三·八聯盟」(the March 8 Alliance)和「三·一四聯盟」(the March 14 Alliance)主導的黎巴嫩政治新紀元;近十五年後, 2019年十月起義爆發。這比任何事情都要更清楚地表明,黎巴嫩的歷史時間是有周期的──無論我們現在做什麼都不重要,因為統治階級總會勝出。在一部分抗議者最終移民和/或放棄之前,我們每次只有幾年的機會之窗。
雖然在阿拉伯左派中,團結其他阿拉伯人佔多數的國家是老生常談,但「每個國家都要革命」的呼聲並不是以阿拉伯為中心的。我認為這些女權行動者是有意圖地把思路打開的,把香港、伊朗、伊拉克、沙特阿拉伯、阿爾及利亞、蘇丹、智利、埃及、也門、巴林、敘利亞和巴勒斯坦列為鬥爭同時要席捲的地方。
將這些革命納入我們的想像中,可以讓我們能以不同的步伐開展工作。可以說,這讓我們能夠採用香港的時間性、智利的時間性、伊拉克的時間性和「黑人生命攸關」(Black Lives Matter)的時間性。例如目前,香港抗議和「黑人生命攸關」抗議的緊迫性是顯而易見的。兩者事實上都踐行著時不我待的座右銘。在美國,警察體制必須改革或廢除(是此是彼取決於你的說話對象)。
在香港,抗議者必須穩住陣腳,把中共繼續實施其計劃的代價提高到無法持續的地步。在這兩個地方,勝利的前景仍疑霧重重。白人至上主義在美國仍然根深蒂固,中共也遠未被打敗。
我相信,每一次成功的起義之前都有一系列「失敗」的起義;無論發生什麼事情,因為鬥爭過,我們現在比當時還是更接近我們的目標的。
作為一個黎巴嫩人,眼看著黎巴嫩的抗議活動暫時慢下來,「黑人生命攸關」和香港抗議的緊迫性其實也在激勵我繼續前進。我之所以能夠繼續專注於呼籲廢除黎巴嫩的種族主義卡法拉制度,是因為「黑人生命攸關」和香港抗議的激勵。解放的勢頭永不消逝,只是不同時間地點起勢有快有慢罷了。
超越周期時間的思考也讓我們能夠理解所謂失敗的抗議運動的重要作用。我相信,每一次成功的起義之前都有一系列「失敗」的起義;無論發生什麼事情,因為鬥爭過,我們現在比當時還是更接近我們的目標的。
在黎巴嫩,十月起義之前舉行了全國大選,數量空前的獨立候選人被動員參選。他們「敗」選了,但也多虧了2015年失敗的「你爛臭了」運動才能有這次「失敗」。反過來,「你爛臭了」運動之所以可能,也是得益於過去多年來教師、學生和各種工人群體「失敗」的抗議。沒有這些失敗,我們就不會有2019年十月。所以,如果這場運動也「失敗」了,接下來其實有可能發生更令人印象深刻的事情。
假設十月起義失敗了。在等待下一次起義的同時,我們該怎麼辦?我認為答案是不要等待。我們已經看到在2019年成功做到了2015年沒有做到的事情。比如,我們在2019年對「暴力」的容忍度甚至接受度比2015年高得多。我們明白打砸搶並不只是反常現象,而是對幾十年不公義的反應,就算讓人不適,也是非常可以理解的。
今天,我們更能看清「常態」本身就是一系列的掠奪:上層階級對勞動群眾的掠奪。去年十月,我們看到整個工人階級和中產階級比2015年更加團結,從而保證了運動的持久性。
流亡、移民和連結的新可能
流傘:越來越多的香港人正因為政治處境惡化的緣故移民。離散、流亡和移民的經歷是怎麼塑造你對黎巴嫩起義的理解的?
EJA:我的祖父在巴勒斯坦大流亡(譯註:the Palestinian Nakba;或稱the Palestinian exodus)中倖存下來,但他從未談及這段經歷。他的一生充滿了痛苦和磨難──畢竟他經歷了黎巴嫩所有的動盪周期。我慢慢意識到,我其實一直不自覺地帶著我祖父的影響投身於每一場抗爭。通過抗議,我在努力避免落得他那樣的下場。我們這一代人正在努力避免落得我們父輩和祖輩那樣的下場──這是這次起義一個巨大的、不為人知的推動力。

某種程度上說,黎巴嫩是一個由移民潮深刻塑造的國家。從很小的時候起,我們的父母就告訴我們,我們終將不得不離開這個國度。他們叫我們在獲得文憑之餘還要尋求第二國籍。這是因為沒有人真正為明天打算──我們成長於持續的生存危機,也就是一些學者所謂的「預見暴力」(anticipation of violence)的狀態。
出於這個原因,我在法國降生(我父母在戰爭結束時離開了黎巴嫩)並擁有阿根廷國籍(我曾祖父從奧斯曼土耳其逃到了美洲),儘管我在黎巴嫩長大(我母親在戰後回到黎巴嫩),就讀黎巴嫩講法語和英語的學校和大學,而且會講黎巴嫩阿拉伯語。
回到先前的一個觀點,僅憑我們很多人生活在其他國家或持有這些國家的護照這一點,黎巴嫩人就應當投入並致力於「每個國家都要革命」的事業。無論我們自知與否,我們都深受世界大事的影響。我猜想香港人的情況也是一樣的。
主導性敘事和假反帝
流傘:有時左派會控訴香港抗爭者受境外勢力資助,擾亂政權。黎巴嫩有類似的情況嗎?
EJA:教派分權協議意味著人們必須求助於他們的教派代表才能讓自己的聲音被聽到。2 除了教派社群內存在的主導性敘事(hegemonic narratives),還有所謂的「境外影響」問題。要理解這一點,你必須理解巴(勒斯坦)以(色列)衝突以及敘利亞和以色列佔領黎巴嫩這一更廣泛的背景。
目前,真主黨可以說是黎巴嫩政治中的主導黨派。由於其軍事力量,它事實上也支配著各大要職(a de-facto kingmaker)。它在黎巴嫩實行高度反動的政治,並持續支持敘利亞阿薩德政權。同時,真主黨由於在對抗以色列的軍事行動中取得的成功,受到西方左翼中的「反帝國主義」專制主義者(“anti-imperialist” authoritarians on the Western left )所敬重。
由於這般只致力於言辭上的反帝主義,真主黨及其支持者特別痴迷於抹黑黎巴嫩抗議者受外國、親美或沙特勢力資助。這些「反帝主義者」往往就是在網上指責香港人受反華勢力資助的那撥人。3
僅憑我們很多人生活在其他國家或持有這些國家的護照這一點,黎巴嫩人就應當投入並致力於「每個國家都要革命」的事業。我猜想香港人的情況也是一樣的。
歸根結底,這些所謂的「反帝主義者」有兩個共同點:一,他們反對美國政府;二,他們想要對複雜問題有簡化解答。確實有阿拉伯人、伊朗人或中國人願意為他們先入為主的觀念提供證詞,讓這些「反帝主義者」免於種族主義的指控──我們可以把這嘲諷地說成「我有一個xx籍/裔朋友」的反帝國主義敘事模式。
與此同時,這些人根本上卻不願意傾聽這些國家的鬥爭參與者闡述別樣的政治未來。這就是這一切的諷刺之處:他們的反帝主義其實依賴帝國主義的邏輯。
就我們而言,黎巴嫩反政府抗議者很快就指出,一個完全依附和效忠於伊朗的政黨指責黎巴嫩抗議者「里通外國」,是相當諷刺的。對這些指責──也是站在真主黨及其盟友一邊的電視台提出的指責──我們的回應主要就是嘲笑。我們曾分發了貼有「美國政府資助」標籤的三明治,還拍攝了讓隨機路遇的抗議者宣稱「我在資助革命」的視頻。
「革命的延續」:未來的志向
流傘:你對黎巴嫩正在持續的起義的什麼方面感到興奮?
JA:主要有兩個方面:女權運動和廢除卡法拉制運動。這兩場運動不符合任何傳統的左翼政治或反教派政治,因為即使是佔主導地位的反教派團體往往也由男性主導,而且主導者總是黎巴嫩籍公民,把黎巴嫩境內相當比例的非黎巴嫩籍居民被排除在外。這兩場運動也不能輕易地融入選舉政治或主流街頭政治。正因此,這些鬥爭能夠讓我們重新想像黎巴嫩可以成為怎樣的一個國家。
我對這些運動感興趣,因為我真心相信,最有效的持久政治變革是那些不符合既有敘事的變革。黎巴嫩史學作品幾乎都預設了黎巴嫩歷史就是黎巴嫩男人的歷史,也就是說黎巴嫩婦女和非黎巴嫩籍/裔男女基本上被隱形了。我認為,把這兩場鬥爭置於黎巴嫩政治前台是解決父權制和宗派主義的交叉問題(intersection)最有效的辦法之一。
流傘:你還有什麼想分享的嗎?
EJA:我從十五年前、十幾歲開始參加抗議。至今,我絕大多數朋友都離開了黎巴嫩。抗議者們知道,可能未來的幾十年裡我們都會一直做這些事,這想想就令人疲憊。當中我學到的是,我們必須照顧好自己,照顧自己的心理健康,以免精疲力竭。同時,我們也要記得為後代、為不同語境下的人轉譯我們的經驗。如今,世界各地的抗議者必須同時也是轉譯者,從一種語言轉譯到另一種語言,把一種經驗轉譯成另一種經驗。
香港和黎巴嫩之間有太多看似偶然的巧合。但從根本上說,我們都是被全球權力和資本體系踏在腳下的土地。擺脫資本與帝國的未來的關鍵在於保持今天這樣的對話,以集體解放為目標。
註腳
[1] 香港人和黎巴嫩人都有一種跨越世代的時間焦慮。1997年回歸時或之後出生的香港人的前途越來越不明朗。至於黎巴嫩,我們通常會按戰爭區分世代:我們的父輩和祖輩在內戰期間長大,或當時已經成年;戰後一代成長於90年代;Z世代在2005年以來的暗殺潮中長大。我和我的朋友成長於一個據稱是和平的國家,但這個國家卻經歷了數十次暗殺、一場重大戰爭(2006年,參戰雙方為以色列和真主黨)、一場重大衝突(2008年真主黨入侵貝魯特和黎巴嫩山的部分地區)以及2011年起義──尤其是敘利亞革命──對黎巴嫩政治局勢的衝擊。每一代人都有類似的生存焦慮,不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
[2] 教派分權協議對人們的生活有切身的影響。例如,作為一個公開反對阿薩德的人,我在黎巴嫩的基督教/遜尼派/德魯茲派佔多數的地區比在什葉派佔多數的地區更安全。這與什葉派、基督徒、遜尼派或德魯茲派(Druze)無關。相反,這是因為黎巴嫩教派體系中的主要什葉派政黨真主黨既擁有大量武裝,又為阿薩德政權的生存投入了大量資源。正因他們在「他們」領地的霸權存在,我在某些地方拜訪朋友時必須採取某些預防措施。↩
[3] 指控黎巴嫩人受外國資助的「反帝國主義者」,也正是那些指控反阿薩德的敘利亞人是穆斯林極端分子的人。諷刺的是,這僅僅是因為真主黨(和阿薩德)利用(instrumentalization)了9/11事件後的「反恐戰爭」邏輯:這種邏輯給所有意識形態敵人都貼上恐怖分子的標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