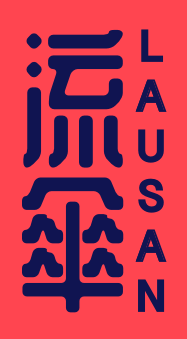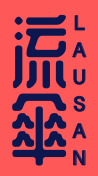這文章原本以中文發表於立場新聞。 香港警方 2021 年 12 月 30 日向立場新聞進行突襲執法行動,拘捕多名立場高層。立場新聞無法繼續運作,被迫關閉。 我們決定在這裡重新發表這篇文章。有關腳註,請參閱英文版本。
譯者:張泳、徐詠然、WF、SC
「無大台」運動強調將決策權回歸群眾;美國勞工理論家金·穆迪(Kim Moody)同樣相信工運應由基層勞動人民、而非政黨或脫離群眾的官僚工會高層帶領,他更發起了在推動工會教育和工人行動上有重大影響的組織「勞工筆記」(Labor Notes)。職工盟2019年翻譯了「勞工筆記」編撰的《成功組織者的八堂課》一書,受部分工會組織者歡迎。
美國的勞工運動對香港有什麼啟示?在本文中,流傘成員Promise Li先簡介美國勞工歷史,指激進基層工人運動於40-50年代漸因工會官僚化而衰敗,勞資矛盾被貶為個體法律事件,工人因而面對愈加激烈的打壓。
作者進而介紹穆迪提倡的「基層工人組織策略」,其重點包括建設以職場為重心的基層組織、找出備受信賴的工人領袖作行動先鋒,就廣泛的工人階級問題進行抗爭,並提升工會成員的階級意識。作者認為因地制宜地運用此策略,可以擊中政商聯盟的弱點,並在尊重群眾主體性之餘,堅定地對社會現況作出準確分析。
大規模流行的新冠肺炎揭示了美國長久以來的「民主」真相:在全球大危機下,從緊急醫療體制如何運作,到對職場中基本權利的訴求,工人和其他邊緣群體都往往無法保障他們的權益。雖然工會往往被視為工人爭取權利的平台,但美國勞工統計局於 2019的報告卻指出工會會員的數目跌至歷史新低,工會密度只有10.3% 。近年,我們見證在特朗普政府管治下,一個在工人推動下的潛在歷史性浪潮,他們正在挑戰受不利勞工條件保護的僱主。我們如何理解美國勞工的歷史背景和當前狀況?在本文中,我將會簡單介紹美國工運歷史,並解釋「基層工人組織策略」(the rank-and-file strategy)如何為美國以至其他地區的工人運動及群眾運動提供參考。
去年香港抗爭運動當中,其中一個突出的特點是示威者頻繁地向美國尋求支持。一方面,美國確實有對香港運動表示支持,但另一方面,美國的精英們長久以來卻一直獲益於中共對香港的經濟剝削,以及和經濟剝削密不可分的政治壓迫。然而,這並不代表香港人要放棄「國際線」,而是我們需要建立一套對美國社會和政治的新分析,從而更好地了解真正的政治力量是如何由日常工人和群眾運動中組織和產生,而不是由國會或行政部門的閉門會議而來。與此同時,我們需要改變對自身運動的理解,以透過新的方法和美國社會連結並得到支持,並向美國群眾點出運動中如新工會浪潮之類的群眾動能,為何在面對國家壓迫時具有最大的變革潛力。
美國勞動法:拒視勞資矛盾為階級問題
簡而言之,美國勞動法將勞工爭議重新定義為個人權利問題和黨派之間的衝突,而不是階級衝突的根本癥狀。執行美國勞工法的國家勞工關係委員會(The National Labor Relations)是由現任總統直接任命,它作為無黨派的特別利益團體,其功能的特徵之一是將勞資問題變成兩方之間的個別事件、又或僅僅只是僱主和工人爭取各自權利的衝突,而不是將它們視為體現結構性問題的癥狀及抵制。 正如勞工學者巴里·艾德林(Barry Eidlin)所寫,「勞動法成為了政治足球,由民主黨和共和黨的負責人輪流推翻彼此的決定。但是這種來來回回的政治技倆,結果是傾向於管理層的方向。審查NLRB裁決的法院傾向於對法律進行狹義的解讀,將僱主的財產權置於工人的集體權利之上。」[1]另一方面,工會領䄂大多數時候很樂意服從在這種安排,用勞資合作代替工人運動帶來基進變革的能力。
伴隨著工人的組織和權益的衰退,美國工會不再是為工人爭取更好待遇的民主工具,而是犧牲了許多工人的主要武器——包括多種罷工——而換來了長期談判協議、定期的工資、增加福利以及工作保障,這種做法直接地引致了工會組織及權益的衰敗。它們已成為史丹利·阿羅諾維茨(Stanley Aronowitz)所說的「一組以公司為導向的機構,充其量只能起著類似於私人福利服務機構的作用」。[2] 民主黨竭力維護官僚化的工會,確保它不受基層民主工運左右之時,共和黨則代表著企業利益,強硬地反對工人權益。特朗普在任內大力剝奪基本工人權益,他在國家勞工關係委員會內,大量任命親管理層與反工會的專家以打擊工人談判權,包括阻撓公開工會選舉,以及在新冠疫情高峰期間,拒讓上百萬名急救員和醫護人員申請有薪假。
美國勞工史:基層鬥爭崛起、工會官僚化增打壓
美國勞工政治的現狀由來已久,而身處香港的我們可以參考美國工運過去及現在的發展,以為香港工人階級建構更好的選擇。
在1870和80年代具鬥爭性的工人運動起義之後,美國勞工運動開始圍繞著兩個意識形態的極點凝聚:一個極點是以塞繆爾·岡伯斯(Samuel Gompers)為代表的「純樸工會主義」(pure-and-simple unionism)和在美國勞工聯合會(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 AFL)中迅速發展的工會官僚主義,這是當今官僚對商業友好的工會主義(bureaucratic business-friendly unionism)的前身。該主義將工人利益在現有的資本主義制度中歸結為「無黨派」的務實改革,不再以一個階級來爭取政治權力。
另一極沿襲自早期勞工團體,例如勞工騎士團(Knights of Labor)推崇的「勞工共和主義」(labor republicanism)民主理想,這些思想後來由激進左派推進,推動普通工人在工會內以至政治領域上爭取權力。尤金·德布斯(Eugene Debs)的社會黨(Socialist Party)、世界無政府主義者工業工人(Industrial Workers of the World, IWW ),以及後來的工會教育同盟(Trade Union Educational League, TUEL)的抗爭派分子,將各種激進的工會主義者聚集在同一平台上,繼續培養這種精神 。
在大蕭條的背景下,基層工人鬥爭(rank-and-file militancy)在1930年代達到了鼎盛時期[3]。1934年左右,明尼阿波利斯的卡車司機、西岸的碼頭裝卸工人和托萊多的汽車工人掀起了罷工潮,並違背了保守派工會官僚的意願,在美國政治中開展了工業工會主義(industrial unionism)的力量,並帶領了產業工會聯合會(Congress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s, CIO)崛起[4]。這些行動大部分是由職場中的左翼人士發起,他們都在組織並激勵其他同事,在工廠內擔起集體領袖的角色。正如米卡·烏特里希特(Micah Uetricht)和艾德琳(Eidlin)重點提出,這些行動的成功並非源自進步的政策或受薪工會幹事;相反,「工人是在法律環境最為嚴苛的情況下取得了最大的成果:這些行動在現代集體談判權體系建立前的1930年代急劇上升。」[5]在此隨後十年中,激進工人分子乘著這些基層的勝利,使大企業不得已採取防守策略,迫使總統富蘭克林在談判桌上,倡導一系列的進步勞工改革。
但是,進步工人階級後來選擇與民主黨緊密聯盟,卻成為了其衰落的根源。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工會、甚至是CIO領導層逐漸與民主黨的官僚機構結盟,與大眾工薪階層變得愈來愈疏離。工會領導人為支持戰爭而壓制了工人們領導的罷工,而在總統羅斯福之後的幾年裡,大企業開展了報復行為。在1945-6年間一場接近總罷工的行動之後,反工會的保守派和國會裡的民主黨人推動了《塔夫脫-哈特利法案》(Taft-Hartley Act),大大削弱了工會的權力、使各種罷工成為非法活動,並擴大了「工作權」(right-to-work),以讓工人能以 「選擇 」不交工會費為幌子,增加了工人透過工會作集體談判的難度。大約在這段時間,工會官僚和政治領袖之間的聯盟,開始形成我們今天所看到的狀況:來自下層的鬥爭性工會主義讓路,以讓國家機器和民主黨作出更緊密的結合。CIO將其陣線中的抗爭派分子清除,而它與基層工人的進一步疏離,令工人們在政府牽頭清算左翼分子的紅色恐慌時期(the Red Scare)變得更脆弱。1955年,AFL和CIO的歷史性合併,加速了以組織為運動方針的衰落:它們開始擁抱「服務勞工」此局部的使命,並視之為一種特殊權益,而非階級政治運動的基礎。
20世紀後半葉,僱主持續狙擊工人權利,以去工業化和「去技術化」等手段進一步打擊工人,例如羅納德·列根(Ronald Reagan)於1981年對空中交通管制員罷工的鎮壓;但工人們也不是束手就擒。尤其是在70年代,對這些打壓最有效的反抗,並非來自民主黨人或工會官僚,而是來自基層人民。由普通工人組成的改革決策會議,通過選舉新的領導層來推動激進的工會改革,例如「礦工爭民主」(Miners for Democracy)、卡車司機爭取民主工會、洛杉磯的「為清潔工爭正義」(Justice for Janitors),以及後來組成了革命黑人工人聯盟(League of Revolutionary Black Workers)的底特律獨立「工會運動 」[6]。但是與30年代不同,正如勞工理論家金·穆迪(Kim Moody)所寫,這些倡議缺乏那種「在運動和階級之間運作,共同發揮集體力量以推進運動」的動力[7]。
如今,我們看到了僱主對工人越來越強的打壓;僱主們設法讓工作變得更不穩定,並尋找能降低工資之餘,又能提高生產率的方法。「精益生產」(lean production)或被邁克·帕克(Mike Parker)和簡·斯洛特(Jane Slaughter)稱為「施壓管理法」(management-by-stress)的方法提倡將職場效率最大化,直至生產鏈或工作流程上的薄弱點被推向臨界點,從而重組並改善系統[8]。這些策略被越來越多學校和教育計劃,如「為美國而教育」(Teach For America)採用,當中的教師流失率很高[9]。在「團隊合作」和「創新」的榥子下,這個思潮更推動了各種生物識別和職場監視工具的發展,同時換來了更高的工人剝削和倦怠率。最近,2018年的Janus vs. AFSCME 裁決嚴重削弱了公共部門工會的議價能力,而去年的加利福尼亞州22號提案(Prop 22)爭議將影響零工工作者未來的議價能力[10]。面對這種情況,民主黨仍樂於繼續參與本質上對勞工不利的政治框架裡。
與此同時,即使沒有強大的工會架構或進步的法律,我們卻都看到了廣泛的工人鬥爭 。威訊通訊 (Verizon Communications)員工就公司削減福利作出反擊,反抗工會早於2016的讓步[11]。儘管西弗吉尼亞州的教師身處在共和黨控制的州份,他們反對其工會主席默許政策改變,並在2018年發起了一場激動人心的罷工,以抵制工資減幅[12]。芝加哥和洛杉磯的教師在基層改革者的領導下,在反對教育私有化方面也取得了類似的成就。綜觀2020年,各行各業的野貓式罷工比比皆是,以回應公司無視保障合理工作條件的行為[13]。
何謂基層工人組織策略?
穆迪通過研究這些工人底層抗爭,建構起「基層工人組織策略」這個概念。它從70年代發展,並在2001年由社會主義組織團結社(Solidarity)發行的小冊子中,首次編纂成文。[14]正如他在最新的解說中提到,穆迪對這一策略的總結包括:發展
「基層組織和主要建基於工作場所的行動(儘管並不局限於此),目的是在與資本的衝突中建立真正的工人力量、爭取改變工會的官僚性質、突破有限的議價限制,並在廣泛的工人階級問題中抗爭、在勞工階級裡對抗種族和性別帶來的分歧、對抗親資本家的商業工會主義(business unionism)及大多數美國工會官僚主義的既有做法,並就著工人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地位及集體擁有的權力,提高工會成員的相關意識。」[15]
「基層工人組織策略」的其他擁護者強調「激進少數派」基層工人的顯著作用,他們在工作場所內——即勞方和資本的張力最為明顯的地方——激勵其他工人以實現上述目標。穆迪寫道:「工作場所是⋯⋯工人最有權依照他們階級意識行事的地方,無論其來源是什麼。」而且,激進少數派工人不是先鋒派領䄂,亦不是最「極端」的、企圖為某些平台或政黨宣傳的人。相反,正如艾德林所寫,激進少數派是「由受人尊敬、值得信賴和行動積極的職場領袖組成,這些人被視為可靠信息和建議的來源,他們有能力推動同行,採取行動。」[16]這一戰略的關鍵,是賦予基層工人以集體和民主方式推動變革和發揮領導作用的權力。雖然基層工人組織策略不限於工會,穆迪解釋這策略必不可少,因為它們「將人們聚集在生產社會關係的重心⋯⋯除了那些由階級鬥爭爆發為公開的政治衝突的極少數情況外,勞動者和資本之間在職場中的角力最為尖銳,也最為反覆。」換句話說,工會之所以重要,並不是因為工會是所謂讓普通人擁有最大權力的、被美化的理想空間;相反,正如我們在美國歷史上所看到的那樣,工會受到協作主義者(collaborationist)和官僚主義的因素阻撓,它們與商業利益結盟且背叛工人階級民主,而且在其他政體中,工會甚至被國家機器更明顯地用作鎮壓工具。穆迪之所以認為工會是必要的,是因為工會是現代民主的矛盾最顯而易見的地點:無論你是否可以投選你的民選官員,那些為工資而工作的人總被那些不受工資困擾的人限制民主實踐的可能。沒有一個民主的計劃經濟和社會,一個人的自由和生計總是最終取決於他創造資本的能力,而這有違公義。
回應對基層工人組織策略的批評
基層工人組織策略提出的是全盤的政治計劃,而不僅僅是狹隘的策略,目的是最有效地爭取日常勞動者的即時需求,以及更公平的社會此宏大願景。近來對該策略的批評指責,它低估了爭取更好的受薪工會幹事或民選領袖的作用,過份強調工會相比工人中心等非正式工人組織的重要性,並重視「反叛黨團」(insurgent caucusing)多於奪取勞工界別機器[17]。然而,這些批評者將該策略看得過份教條化,而忽略了擬定該策略時的意識形態基礎。正如穆迪所指出,基層工人組織策略支持組織化的工人所採取的各種行動: 請願、合同運動、出版、核心小組、直接行動、工會選舉和培訓課程等。此外,穆迪和其他支持者一樣認為「過渡組織」是重要的,這些組織可以是工會內部的基層工人改革核心小組,以至特定種族的社區組織。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凱特·道爾—格里菲思(Kate Doyle-Griffiths)闡述了這些過渡組織在基層工人組織策略中的重要性,並指出它們
「在社會運動停頓時帶來延續性,並在組織化的工人運動中進行政治教育,不像在資產階級政治那樣把問題視為『分裂性的』文化戰爭風暴,而視之為同事、家庭和社區成員日常生活要面對的實際問題。他們也可以支持職場、租戶和其他的形式,成為跨界別、跨抗爭舞台的政治中心。」[18]
換句話說,基層工人組織策略主要以各種手段,具體地賦予普通工人權力,讓他們以自己的話語和社會背景,意識到自己的階級力量。這可能意味著在一個城市,一群當地工人聚集在一起,支持和組織並未加入工會、面對被驅逐之威脅的移民工;也可以是在另一個城市,有人在現有的工會裡成立一個改革核心小組。一個重要的例子是穆迪本人有份創建的組織「勞工筆記」 (Labor Notes);它是一個過渡組織,通過政治教育、製作節目和報導,建立基層工人的意識。它通過節目將基層工人召集在一起,以便他們可以從彼此的抗爭、成功和錯誤的經歷中學習。事實上,組織者可以擬定策略性優次,來決定應組織的工種,正如過去有人嘗試找出策略性重點行業(如教育)去組織一樣[19]。但是,這些優次並非一成不變,而是根據對每個地方或國家的環境中,仔細、具體地分析資本的弱點而得出。這使它成為一種策略,而不僅是一種手段。
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可以理解基層工人組織策略並不必然排除出任專業的組織者業務(例如受薪工會幹事、非政府工人組織)的可能。然而,按照這策略對於工會在資本主義結構中的地位之分析,專業化並不是建立運動最重要的方法。正如穆迪所解釋:
「根據定義,很多員工未能與基層工人建立長遠而緊密的關係,例如經常從一場運動轉到另一個運動的研究人員和組織人士,他們不能體會到基層工人長期且日常所面對的管理層壓力、發起未經許可的行動,或參加反對運動。即使他們同情基層工人運動,但他們的地位與基層仍維持著一定的距離。」
基層工人喬·埃維卡(Joe Evica)指出,受薪工會幹事和官僚機構的工作內容,正好是為了維持法律所規定的典型談判程序;正如我們所指出,這種談判程序一開始就對工人利益極為不利。因此,「在常規的談判過程中,職場行動的和基層工人活動看上去是對既有程序的干擾,而非工人可用以擴大權力和控制權的主要手段。」[20]從這個意義上看,該策略並不反對人出任受薪工會幹事,只是堅持應優先考慮組織基層工人。
同樣的道理,也適用於競選工會領導層的工人,或支持有關進步勞工法案的投票倡議。基層工人組織策略並不反對基層工人參加工會選舉,或爭取更有利的工作環境以便繼續組織。但它確實表明這些事情本身,並非最有效地為工人爭取民主的即時或長期解決方案。它試圖反駁的觀點是:勞動改革或新的組織技術才是推動可持續和激進改革的動力。正如烏特里希特和艾德林簡潔地指出,「惡劣的法律框架並沒有阻止工人階級的崛起;反而,崛起的工人階級造就了沒那麼惡劣的法律框架。」實際上,歷史告訴我們,將組織權力集中化、專業化到個別與基層工人分離的人身上,是許多激進工人運動衰退的原因。如果基層工人不獲賦權去自行組織,這些曾一度充沛的抗爭力量通常很快就會消散。而且,1930年代的經驗告訴我們,工人勝利的高峰通常是在專職的組織者出現之前形成,而非之後。這些自發的勝利,往往是結構性或立法性變革的先決條件。
對群眾政治運動的啓發
長遠來看,到底基層工人組織策略能夠如何豐富可以有效地挑戰整個資本主義制度的、更大型的群眾主導政治運動呢?從爭取黑人性命的運動,到泰國、法國、香港、波多黎各和白俄羅斯的抗爭,我們所身處的時代裡,對現狀最具威脅的群眾運動往往是無領䄂且去中心化的。穆迪提出,我們需要把各社群中的基層活動集結起來,建立一「更廣泛的階級意識、或走向獨立工人階級政治的運動。」但是,對於21世紀的許多當代群眾運動而言,這種集中化的形式是令人生厭或陌生的。因此,基層工人組織策略其中一個最大的挑戰,就是要走進廣泛群眾政治,對新的抗爭場域下產生的不同組織形態保持開放性。而沒有政黨或官僚等體制化政治,是否就能避免分裂呢?基層工人組織策略正好提供了一定的自由度,可以在各種環境中尊重運動的自主權,同時無需摒棄對核心的結構性問題作出清楚分析。
這種精神與我們香港的政治局勢息息相關,並為近來許多「無大台」運動常見的意識形態混亂問題提供了一條出路。這策略所提供的,並非一條讓工人遵循的政綱或政治路線,而是提供了一個普遍的框架,讓普通工人找到壓迫他們的源頭和其弱點,並明白到他們在各自職場或地區內,以階級為單位集體組織起來爭取權力,就是最有效的政治反抗。這意味著工人可以建立一個沒有領袖、同時並非沒有意識形態目標的群眾運動。我們必須把兩者劃清界限:沒有領袖和教條可以成為優勢,但對壓迫自身的製度、以及何種組織形式最能打擊其弱點缺乏清楚的分析,是對於民主抗爭的局限。這意味著我們絕不能迴避發展基層工人組織策略,朝著建立過渡性組織的方向發展,以對結構性不公義的現象進行分析,促進跨行業和地區的政治協作。這可以包括基層組織、民主辯論論壇、技能分享論壇、跨工會組織,工人中心等。香港基層工人組織策略並不意味著縮窄橫跨整個公民社會、帶來群眾運動的政治聯盟,而是建構一個具戰略性和務實的政治聯盟,優先建立最能對抗中共官僚資本主義最弱點的組織力量。要做到這一點,我們需要對制度和群眾運動如何運作有清晰的政治理解,並不能忽視我們的運動由甚麼勢力構成的問題。
在中國等非自由專制國家,最佳的工人組織策略會相當不同,但是基層勞動人民的力量依然是一個有用於抵抗此極權的工具。最近的一項研究表明,「工業工人一直是民主化的關鍵推手,其角色甚至比城市中產階級更為重要。當工業工人動員群眾起義對抗獨裁政權,政權的民主化往往指日可待。」去年緬甸的一個大罷工涉及政府,醫療,與鐵路工人,對新成立的軍政府作出全面癱瘓國家機器的重大威脅,極度升級歷史悠久的反軍事政變社運抗爭能力。緬甸社運人士林梭昂指出,緬甸軍方 「從持續的經濟主導地位中奪回了政治權力。」 緬甸最近的經濟倒退混淆緬甸軍方發揮於緬甸全國民主聯盟統治下發展的經濟資源和前景的極度中央化控制。這些經濟資源和前景包括由本地農產業產生的資本流動, 以及緬甸軍政府對於中共 「一帶一路」 擴張政策的踴躍歡迎態度。緬甸作為一個非民主政體,同時體現於全國民主聯盟的世襲權力體系以及其與軍方及資本家之間的妥協關係(縱使這關係極其不穩定)。綜合以上分析,動員基層勞工,可能正正是容許這場運動不僅止步於逆轉這場政變而是直搗政權權力核心的轉機。
在全球資本主義中,雖然職場是我們的自由最受限制的地方,但在不同地方,國家、僱主和廣大工人運動之間的關係存在很大差異。一些政權不保證工人擁有集體談判或成立獨立工會的權利。因應各種管治制度,基層工人組織策略表現出來也會大有不同,但也能幫助我們理解工人鬥爭的關鍵場所和方式,以爭取即時的權益,也為一場可以達致長遠、可持續且有效的自由之運動打下根基。從美國等西方政府到第三世界的獨裁政權,如果不從根本上認清勞工與資本之間的矛盾,即使是從選舉權到基礎設施建設等政策都得到落實,各種不同的壓迫也會繼續存在。綜觀各場爭取「自決」的運動——特別是我們在香港和別處看到的那些——當受薪工人的經濟自由和權力再分配得不到保障時,他們的民主夢想就受到了限制。基層工人組織策略主張:邁向解放的道路並非從選票或武器開始,而是從辦公室工人、零售工人,到家庭主婦和自由職業者等的一眾普通工人,在職場上向國家和資本的壓迫架構發起挑戰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