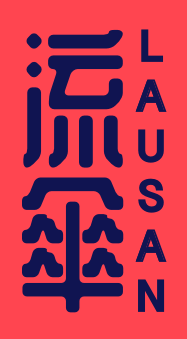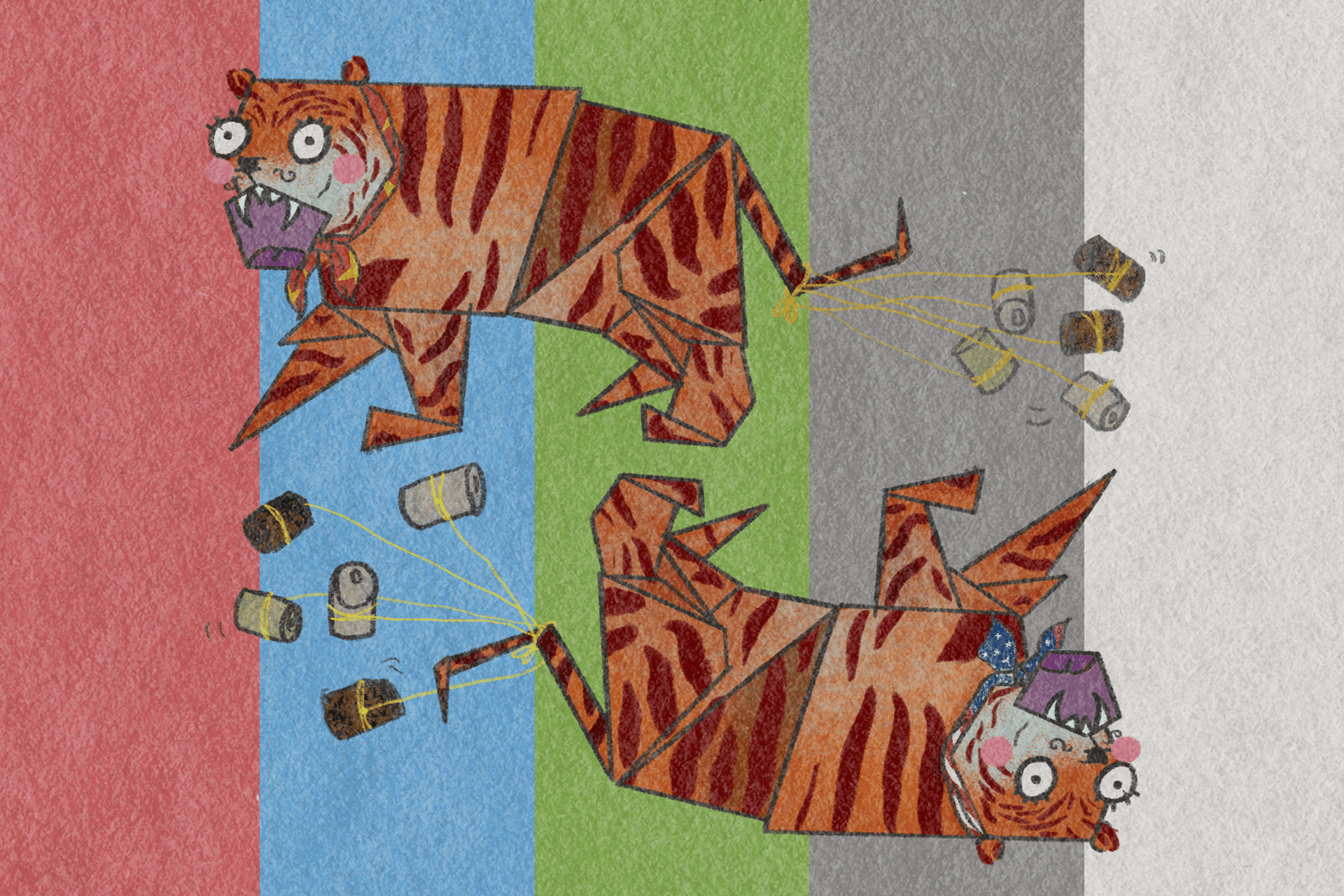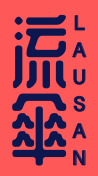譯按:本文原刊於美國左翼期刊 《幽靈》。流傘獲授權自行發布。詳情請聯絡流傘義務翻譯團隊。
譯者:Paradoxite
二十一世紀的中國是個資本主義社會。對於一個在1950年代末基本消除了生產資料私有製,又在後一個十年裡進行了二十世紀一些最激進的政治實驗的國家來說,這是個巨大的轉變。儘管生產關係在過去四十年受到了深刻改組,但中國共產黨仍然持續著壟斷權力,並仍公然自稱為社會主義者──只不過現在掌權模式具有「中國特色」。
中國由共產主義走向資本主義的道路導致了中國國內和國際左派嚴重困惑:左派應該如何定性現狀?澄清中國姓資姓社的問題對於反資本主義實踐來說至關重要,而中國在國際上日益增長的力量更加凸顯這一重要性。這個問題歸根結底是,我們是否相信中國政府及其對抗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的戰略代表了一種解放政治。另一方面,如果我們不把中國看作是在嘗試超越資本主義,而是陷於一場與美國競爭國際霸權的纏鬥,就會得到一個非常不同的政治結論:我們必須獨立於並反對所有現存國家勢力,制定我們自己的激進解放路線。
資本主義是一個複雜得出名的概念,我在這裡只能談談其中某些核心問題。從根本上說,它是一個將人的需要附屬於價值生產的制度。這種附屬關係通過市場依賴的普遍推廣而被制度化,與此同時商品形式亦成為人與人之間關係的中介。這種資本邏輯不僅表現在對勞動者的經濟剝削和隨之而來的階級社會關係中,還表現在工作場所、國家和其他場域的政治統治模式中。儘管與自由主義的英美模式有重要區別,但我們將看到,中國在方方面面都已成為一個資本主義社會。
中國資本主義屬性的標誌比比皆是。法拉利跑車和古馳商店裝點著中國的各大都市,國內外公司的商標印滿了天際線,高層豪華住宅如雨後春筍般遍布每一個主要城市核心區。中國從世界上貧富最均等的國家之一迅速演變為經濟最不平等的國家之一,暗示了重大的結構性變遷。我們也可以把中國加入世貿組織(WTO)、政府堅持自稱是市場經濟,或者習近平在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為全球化辯護並主張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看作中國正在擁抱資本主義的表態。人們同樣可以發現普遍的文化表現形式下暗藏的資本主義取向,包括提倡刻苦工作、徹頭徹尾的消費主義,以及對喬布斯、馬雲等商界英豪的天才崇拜。
然而,如果把資本主義的這些效應與資本主義本身混為一談,那就錯了。為了更全面地認識資本如何成為中國國家和經濟的指導原則,我們需要做更深入的探究。
經濟、勞動和社會再生產
要提出對資本的徹底批判,我們可以像馬克思那樣,從商品入手。商品是指對某人有用的、包含交換價值的東西。在資本主義生產體系下,交換價值占主導地位,也就是說,決定生產的是利潤,而不是事物的實用性。《資本論》一開篇馬克思就分析了商品形態,因為他相信這可以讓我們解開資本主義制度的全部內涵。
如果我們審視當代中國,毫無疑問,商品生產已經普遍化。這一點在以中國為中心的龐大跨國供應鏈中表現得很明顯。在這條供應鏈上,生產手機、汽車、醫療設備、服裝、家具等各種商品的工廠對中國工人的剝削讓國內外企業富得流油,也帶來了前所未有的出口繁榮。雖然騰訊、阿里巴巴、百度和字節跳動等中國科技巨頭在某些重要的方面不同於矽谷企業,但它們生產以信息商品化為首要導向的技術的努力是一致的。同樣,反復出現的房地產泡沫和開發商大規模盈利表明,住房的生產是為了應對市場機遇。在各大經濟部門中,很明顯,生產首先都是為了創造利潤,而不是為了滿足人的需要。
雖然對商品生產的分析具有啟發性,但從另一個方向來切入這個問題更有政治效力:與其問資本需要什麼來確保自身的不斷擴張,不如問人如何生存。那麼,中國的無產階級──一個唯一擁有的生產性財產就是自己的勞動力的群體──如何確保自己的社會再生產呢?答案是:就像在其他任何資本主義社會,無產階級要想活下去,就必須想辦法依附於資本。食品、住房、教育、醫療、交通等基本需求,以及休閒和社交時間,都不是理所當然得到保障的。相反,在中國,絕大多數人只有首先讓自己對資本有用,這些需求才能得到保障。
農民工一旦離開戶口所在地,就放棄了享受任何國家補貼的再生產權利,實際上也就在自己的祖國淪為二等公民。
當然,中國是一個高度異質的社會,而社會經濟差異亦隨即導致生存策略多樣化。要闡明這個論點,在人口統計學和政治上最相關的群體範疇是農民工。農民工是近三億在非戶口所在地謀生的人口,是一支龐大的勞動力,也是中國產業轉型的中堅力量。農民工一旦離開戶口所在地,就放棄了享受任何國家補貼的再生產權利,實際上也就在自己的祖國淪為二等公民。或許顯而易見的是,數億人做出這一選擇的唯一原因是他們無法在自己貧困的本鄉生存下去,在市場力量的驅使下,不得不到城裡打工。
資本主義的勞動關係在1970年代末首次在中國出現時,在政治上是有爭議的,因為中共黨內許多人仍然支持毛式「鐵飯碗」終身僱傭制。但到了九十年代,這種爭論就平息了;1994年的《勞動法》為僱傭勞動(wage labor)建立了法律框架,就是最明確的標誌。新政策沒有如許多改革者希望的那樣開啟一個高度規範的社會民主式的勞動力市場,但勞動卻被商品化了,儘管仍有高度非正式性。在特別注重提高合法勞動合同普及率的《勞動合同法》於2008年實施後,簽訂合同的農民工數量在2010年代初甚至還有所下降。截至2016年,只有35.1%的農民工簽有合同。
工人如果沒有合同就不享有法律保護,這樣一來要解決侵犯勞動權利問題就極其困難。此外,社會保險──包括醫療保險、養老保險、工傷保險、失業保險和「生育保險」──是由用人單位繳納的。淪為非正式勞力還會使居住在非戶口所在地的人遭受其他形式的排擠和市場依賴。例如,一個外來務工者想讓自己的孩子入讀城區公立學校,首先要出具本地勞動合同;僅這一條規定就將絕大多數流動人口排除在公立教育之外。雖然教育等名義上的公共產品的分配機制因城市不同而大相徑庭,但總括邏輯是優待那些國家認定對提升當地經濟有用的人。很多大城市都有「積分」計劃,申請人必須在一系列以勞動力市場為導向的指標(如最高學歷、技能認證和「勞動模範」獎)下累積積分,才能享受公共服務。適格者之外的所有人都全憑市場擺佈。
在戶口所在地工作的城市無產者的情況略有不同,從物質角度看他們的情況當然更好。他們能享受公立教育,可能還有一些住房補貼,並且更有可能簽訂有法律約束力的勞動合同。中國的福利待遇並不優厚,社會支出佔GDP的比重遠低於經合組織(OECD)成員國的平均水平,但城市居民享受福利的機會更多。深重的階級和區域不平等以及財政問題困擾著中國整個體系。因此,毫無疑問,即便是這些相對受優待的群體,也必須讓自己對資本有用,才能確保充分的醫療、體面的住房或退休後的保障。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不足以在可為社會接受的水平上支持再生產,也不以此為目的。
政治權力
中國經濟不僅靠資本主義運行,而且現在國家政權也是為資本的總體利益進行統治的。和其他資本主義國家一樣,中國的國家政權也有自己的相對自主性(當然可以爭論哪個國家政權自主性更大)。但足夠明顯的是,中國已經搭上了由資本主義價值驅動的快車──就這一點已經造成國家治理方式的深刻轉變。
這種以資本為中心的邏輯在車間政治中非常明顯。過去三十年裡,中國的工人暴動呈爆炸式增長,野貓式罷工量冠全球。當工人們遵循悠久傳統,拒絕向資本提供勞動時,國家是怎麼應對的?雖然罷工免不了各有特色,但警方幾乎都是代表老闆介入──本國私營企業、外資企業和國有企業都受惠於這等服務。警察或國家支持的暴徒用強製手段破壞罷工的例子不勝枚舉。但其中一個特別突出的例子是警方暴力鎮壓台資裕元鞋廠四萬人罷工;防暴警察擔當台灣資本家走卒的歷史諷刺可逃不過工人的法眼。如果說這次罷工巧妙地提出了「你站在哪一邊?」的問題,中國政府的選擇已經足夠明顯。
國家暴力也施用於對城市公共空間中非正式工人的治安管理。令人憎惡的「城管」──這支1997年為執行非刑事法規成立的準警察部隊──無數次使用令人震驚的強製手段清理街頭小販和其他非正式工人。常態化的警察暴行在中國的非正式勞動者群體中激發了深刻而廣泛的敵意,反城管暴動非常普遍。其中或許最轟動、最暴力的例子發生在2011年廣東增城。當時,風聞一名孕婦在一次城管行動中被毆打致流產後,農民工們集體走上街頭。經過幾天的大規模暴動,人民解放軍更暴力鎮壓了暴動。
雖然罷工免不了各有特色,但警方幾乎都是代表老闆介入──本國私營企業、外資企業和國有企業都受惠於這等服務。
如果我們認為資本不僅僅是一種基於剝削的經濟關係,也是一種政治關係,其中勞動者屈居從屬地位,那麼,中國政府的行為還在其他重要方面符合資本邏輯。正當中國開始資本主義轉型,鄧小平在1982年即決定從憲法中刪除罷工權條款。與這種對勞工權利的限制相配套的,是一直以來對工人自組織的禁止。唯一合法的工會是中華全國總工會。在職場上,這個組織明面上隸屬於中共,暗地裡隸屬於資本。企業人力資源經理被任命為企業級工會主席是標準做法,連做做樣子讓工人進行民主參與的遮羞布都免了。毋庸置疑,工人並不認為這些工會在任何意義上代表了他們的利益,建立自治組織的努力也遭到了嚴厲的打壓。
對無產階級的政治奴役也延伸到正式的國家機構當中。和所有公民一樣,工人們沒有能力在公民社會中自我組織,沒有能力組建政黨,也沒有能力行使任何形式的政治代表權,因此他們只能指望中共會一片好心好意代表他們。中共不再號稱代表工農的利益來對抗他們的階級敵人──自從接納資本家入黨,並在江澤民的領導下推進「三個代表」的理念以來,黨的目標已變成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再加上國家有效禁止承認階級對立,顯然,一黨執政的社會基礎已經發生了深層次的反革命。
即使是粗略地評估中國政府的社會構成也會發現,資本不僅能很好地獲得國家權力,而且從根本上說,它與國家權力是分不開的。第十屆(2003-2008年)全國人大代表中,「一線工人」代表數量降低至2.89%,比上世紀七十年代大幅下降。財閥在全國人大和政協中的驚人集中度最能體現資本政治權力的正規化。截至2018年,這兩個中央政府機構中最富有的153名成員的財富總和約為6,500億美元。立法機構曾試圖吸納那些私營部門的億萬富翁,比如互聯網巨頭騰訊的負責人馬化騰。但經濟和政治權力之間的轉化也在另一個方向上運作:前總理溫家寶的家族利用其政治關係積累了約27億美元的個人財富。在二十一世紀的中國,資本產生政治權力,正如政治權力產生資本。
執政黨宣稱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根本沒有得到現實的印證。不過,中國經濟有幾個特點與當前的資本主義國家模範具相當大的不同,因此值得多加注意。
國家干預經濟
毫無疑問,中國政府對經濟的干預程度比大多數資本主義國家更為廣泛。但如果我們關注的是普遍意義上的資本主義,而不是其相對新穎的新自由主義形式,中國似乎就不那麼特殊了。中國的國有企業貢獻GDP的23-28%,在當今世界無疑是很高的。但對資本主義來說,統制主義(dirigisme)並不是什麼新鮮事:它不僅出現在其誕生地法國,還出現在各種法西斯國家、獨立後的印度,甚至國民黨統治的台灣(台灣的政府經營企業八十年代末就貢獻了本地區近四分之一的GDP)。以提高效率、利潤率和可預測性為導向的國家干預並不與資本主義對立,而更是後者的一個必要組成部分。
重新回到勞動者的角度,我們會發現國有資本和民營資本的差別微乎其微。作為國家「打破鐵飯碗」運動的一部分,1990年代和2000年代初有數千萬國企工人下崗。這種私有化運動把他們手足無措地扔進勞動力市場,導致了這些前國家主人翁的生計危機和大規模抵抗。
這一波裁員和竊取工人養老金及其他公共財產的浪潮過後,剩下的國有企業都受到了「硬預算」和市場力量的制約,包括在勞動制度上。正如社會學家Joel Andreas廣泛紀錄的那樣,毛時代公認不完善的工作場所民主實驗已經被市場化所淘汰,國企工人現在同樣從屬於管理層,和在私人企業沒什麼兩樣。這些企業在任何意義上都不是公共財產──它們屬於並受一個不用負責任的國家所控制。
儘管相信一個新興超級大國會建立我們想要的世界讓人感到欣慰,但這不過是一種幻想。理想的世界必須由我們親自創造。
土地問題與此相關但又有所不同。確實,所有城市土地都歸國家所有,而所有農村土地則是當地居民集體所有。但根據大量研究,使用權與所有權的分離使對地表的使用具有了明確的資本主義性質。這給城市帶來了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商品房建設大繁榮;如上所述,商品房建設完全以市場信號為導向。城市政府在財政上高度依賴土地拍賣的利潤,導致政府利益與開發商利益緊密結合。
持農村戶口者有權獲得一塊土地,但土地面積和質量絕少足夠維持社會再生產,正如人口大規模從農村向城市遷移所暗示的那樣。城市擴張當然亦大規模剝奪農民的土地。和國企工人一樣,農民幾乎沒有能力監督或控制他們(名義上)集體擁有的土地,村幹部亦慣性代表集體說話。結果就是在無休止的土地剝奪循環裡,農民往往只得到其土地市場價值的一小部分,其餘大部分則落入幹部和開發商的腰包。最後,對於那些保有農業用地的人來說,中國的農業已經發生了深刻的資本主義變革:土地使用權鞏固在農業綜合企業手中,同時各種農業投入也被商品化。土地形式上的集體持有對這一進程幾乎形不成阻礙。
資本主義價值生產的邏輯已經深入經濟和國家,極大規模地改造了中國的社會結構。但理解當代中國的階級關係只是第一步。為制定足以應對當前深刻危機的政治對策,有必要更全面地評估階級如何與其他形式基於種族、性別、地域和公民身份的社會等級複雜地相互構成。要解決一系列緊迫的實際問題,不能單靠階級分析,更不能建基於自由主義或民族主義框架的主導。我們應該如何解讀中國政府在政治上扼殺香港社會反抗聲音、吞併台灣的承諾,以及新疆和西藏的漢人殖民工程?一帶一路倡議下全球投資的巨幅增長,是否新興資本主義帝國的表現?對於中美衝突的加劇,怎樣的激進、反民族主義、反帝國主義的回應才是恰當的?
以上是左派當下面臨的一些最緊迫的問題,而這些問題亦沒有簡單的解答。但可以肯定的是,反資本主義者必須全盤拒絕中國政府單方面引領世界步入社會主義將來的虛假承諾。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寫道的話在今天仍然適用:「對我們來說,共產主義不是一個要建立的狀態,不是一個必須現實自我調整來與之適應的理想。我們稱共產主義為廢除現狀的真正的運動。」儘管相信一個新興超級大國會建立我們想要的世界讓人感到欣慰,但這不過是一種幻想。理想的世界必須由我們親自創造。
Eli Friedman是康奈爾大學勞資關係學院國際及比較勞動學副教授。他是《叛亂陷阱:後社會主義中國的勞工政治》(ILR出版社,2014)和《罷工中國:工人抵抗的敘事》(Haymarket,2016)的合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