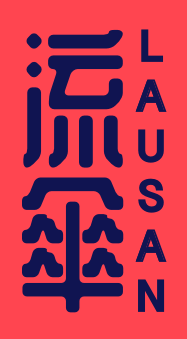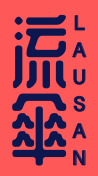本文原刊於《daikon*》;流傘獲授權自行發布。詳情請聯絡流傘義務翻譯團隊。
譯者:K Wong
近兩年來,在我家的短信群組,我爸在喀什的親戚沒發過一條短信。
他們最後所發的一些短信,是他們擁抱中國政府以「堅決打擊暴力恐怖活動」為名、強制他們留守家中為實的照片:在照片中,他們穿上被安排的服裝,擺出笨拙的姿勢和擠出別扭的笑容。此後,我小姨媽發了一條短信,提到她的丈夫下班後沒有回家。很有可能地,他已經被捕。之後,我表兄弟姊妹也傳來短信,那時候,他們說他們在找最快從烏魯木齊、北京、上海、西寧、成都和重慶回家的方法。他們想回到獨自在家的小姨媽身邊,幫她找出所發生的一切的因由。不過,從那以後,我再沒有聽過他們的消息。
我爸的家人是薩里庫爾·帕米爾(Sarikoli Pamiri)後裔的穆斯林,他們是塔什庫爾幹(Tashkurgan)的原住民。塔什庫爾幹位於被中國占領的準噶爾(Dzungarstan)和阿爾蒂沙爾(Altishahr)以西、喀什市的塔什庫爾干塔吉克自治縣 (Taxkorgan Tajik Autonomous County)中。這個地方比較為人所知的名稱,就是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Xinjiang Uighur Autonomous Region,縮寫為 XUAR)」,或是「東突厥斯坦(East Turkestan,縮寫為ET)」。我的姨丈,即是我小姨媽的丈夫,是維吾爾族(Uyghur)和吉爾吉斯族(Kyrgyz)的後裔。
我相信大家已在新聞中看過相關報導:中國政府大規模監禁穆斯林,最明顯的是將維吾爾人送入被稱為「職業技能教育培訓中心」的拘留營,藉此「再教育」穆斯林人士的政治觀,以「打擊恐怖分子」。除了維吾爾人外,涉及的穆斯林,還包括了薩里庫爾人(Sarikoli)、塔什庫爾人(Tashkurgani),瓦罕人(Xik/Wakhi),哈薩克人(Kazakh),吉爾吉斯斯坦人(Kyrgyz),烏茲別克人(Uzbek),撒拉爾人(Salar),古格人(Kachee,即藏回人),撒爾塔人(Santa,即東鄉人),保安人(Bonan),錫伯人(Xibo),裕固人(Yugur),瓦剌人(Oirat),達斡爾人(Daghuur)和其他回族社區。根據報導,營內的「教育」手法層出不窮,例如酷刑、單獨監禁、性暴力、洗腦,還有強迫勞動等等。
以往,國際間並沒有採取任何行動,去提高我們抵抗持續不斷的國家暴力的關注聲音。相反,我們的苦難一直被利用為施行帝國主義特權的象徵。
有鑑於此,視這些地區為家、現今散居海外的民眾紛紛嘗試為家人下落不明而尋找答案。我們一直在呼籲世界去關注對於伊斯蘭教的恐懼和歧視、侵犯人權、種族清洗、種族滅絕,以至漢人沙文主義和中華至上的帝國主義。以前,我們總覺得世界不太在乎。當然有些人會關注這些事情,但這不足以產生足夠力量,讓盟友和其他同夥與我們一起合作,作出反抗。
在主流英語媒體,我們偶爾都可能會讀到一篇有關的報導。有時會很詳細,有時則不會;但這些報導永遠不會成為頭條。會注意到這些新聞的人,通常是那些已經留意、了解並知悉相關情況的讀者,或者那些認識受影響的家庭的人。
2019年7月17日,特朗普會見了在中國受到宗教迫害的受害者。這些受害者請求特朗普採取行動。特朗普的回應極其簡短,許多人相信他對此一無所知。在這天的一星期前,廿二個聯合國大使致函人權理事會主席高利·錫克(Coly Seck)和人權事務高級專員米雪·巴切萊(Michelle Bachelet),就中國政府任意扣押穆斯林一事,呼籲他們敦促該政府就「遵守其國家法律及國際義務,並尊重人權和基本自由」。這是國際間首次對拘留營作出回應。在很大程度上,促成這信聯合國大使請求的,可以歸因於受到中國如此政策影響的海外民眾積所極採取的行動,以及其得到的盟友和同謀的支持。
事實上,拘留營所得到的媒體關注,並非因為這封聯合國大使的信。 相反,這些關注,是在特朗普開會後才發生的。
越來越多提及「新疆」中的維吾爾族和穆斯林的少數群體的報導。但是,這些報導的目的,大多是為了重申中國陰暗的面向,例如她的煽動性、仇外心理和心理文化觀念,藉以加強在貿易戰之下,對於中國作為美國(或西方)經濟威脅的敘述。以往,國際間並沒有採取任何行動,去提高我們抵抗持續不斷的國家暴力的關注聲音。相反,我們的苦難一直被利用為施行帝國主義特權的象徵。特朗普開會後,我們開始看到越來越多的人支持各樣的政治遊說,呼籲對中國實施懲罰性的制裁,以報復大規模拘禁以維吾爾族人為首的穆斯林。
這些反對派觀點令人覺得我們不值得擁有跨國界的團結力量。
流散海外的人組織的行動並不是一個同質的整體;對於相同的議題,不同的小組會有不同的政治觀點。新聞媒體對中國穆斯林持續遭受迫害的關注日益增加;這種變化主要體現在媒體對ETNAM「東土耳其國族覺醒運動」(East Turkestan Nationalist Awakening Movement,簡稱ETNAM)的遊說工作給予不成比例的關注。總部設在華盛頓DC的ETNAM,以擁護右翼聯盟、反共和泛土耳其主義的言論聞名;實際上,這個組織並沒有得到大部分流散海外的維吾爾族人的支持。媒體對於ETNAM的關注,令到不同維吾爾組織所做的工作被誤解為ETNAM一部分。事實上,許多不同的組織都只為實現同一目標;這個目標,就是終結對於他們自己的家人的監禁。
不少在互聯網上有眾多追隨者、自稱是傾向左翼的個體發表不同意見,他們或是全盤否認穆斯林拘留營的存在,或是明確捍衛此類政策。這些言論,當然與他們先前支持廢除監獄、反對全球伊斯蘭恐懼症的工業園區的主張互相矛盾。相對於提高受影響的群體的抵抗聲音,或是分析這些聲音何以在以人道干預為名、以宣揚美國軍事侵略為實的情況下被象徵化和被政治操控,某情度上,這些反對派觀點令人覺得我們不值得擁有跨國界的團結力量。
作為社區組織者,對於我來自的地方,這些觀點尤其令我心碎。我從未見過超越二分思想、超越令我們運動分裂的民族國家政治操縱的參與。相反,跟我發生口角的人,要麼默默退出與我的社區,要麼直接否認事實,要麼轉向一種對中國共產黨完全不批評的政治觀點,然後繼而指責我或是其他人與準噶爾和阿爾蒂沙爾的聯系,以導致反中國的種族主義、反亞洲自我仇恨,以及為中國扣赤色帽子,加以迫害。
「西方」的種族主義及反中國情緒,可以與中國在亞洲社會、政治和經濟有主導地位,以及中國在全球南方(Global South)新殖民主義之下展開各種工業和基礎設施的交易共同存在。另一方面,中國和美國的帝國主義亦可以籍壓迫制度的姿態並存。將拘留營打造成「反恐」政策的說法,與關塔那摩灣海軍基地(Guantanamo Bay Naval Base)內的美軍監獄非常相似,這個事實足以證明上述一點。我曾經信任的人,拒絕面對這些複雜性,實在令我對於建立一個以集體解放為目標的統一陣線的可能性感到悲哀。
要抵抗和摧毀所有壓迫制度是極其混亂的。如果我們想要將鬥爭建立在集體團結的基礎上,就必須堅定地指出我們的歷史何以與暴力交織在一起。我們並不能幹掉生活經驗與我們意識形態不同的人。我們需要繼續建立我們的跨國社區關係,跟在任何地方存在、發生和遭受國家暴力的社區站在一起,保持團結的關係;跟那些可以大膽地表明我們是生活在一個複雜的、具有令我們運動分裂的多重地緣政治利益關係的人站在一起。我們更需要坦白地為各自從其他社區偷來的特權、或將這些特權強加給其他社區而引致傷害負上責任,重新想像跨國社區關係的實踐。
Nurdoukht Khudonazarova Taghdumbashi是一位藝術家、語言學家、耐心的擁護者,也是居住在有色勒庫爾、古格、塔吉克,以及韓國遺產的Ohlone土地的組織者。通過布匹設計,語言分析和美食記憶製作,她希望探究離散分裂化、重奪文化,以及對於歷史留下持續性的殖民創傷等議題。(Instagram: @mandu.mant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