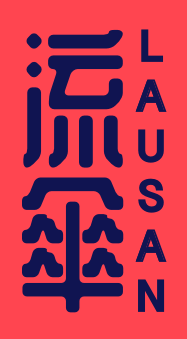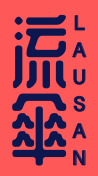隨著中美緊張關係加劇,許多人都在尋找一些歷史隱喻,以描述國際事務現狀。其中一個勢頭強勁的隱喻是將中國比作納粹德國。這隱喻以多種形式呈現,包括「赤納粹(Chinazi)」之類粗俗用語,或稱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為「習特勒(Xitler)」──這都是一種透過與納粹主義聯繫構成羞辱的形式。因著中國政府在新疆開展大規模再教育營,加上其他向維吾爾族和原住民強行種族清洗的措施,所引發的廣泛憤慨得以進一步強化中國與納粹德國之間的聯繫。1
與此同時,人們也越來越關注一些中國知識分子如何對納粹思想家的論說表現出濃厚的興趣,如納粹法學家卡爾·施密特(Carl Schmitt)。施密特反對個人主義、高舉國家至上,以及捍衛中央集權於單一領導人的思想。有趣的是,這些中國知識分子分明都來自左翼傳統,並且屬於諸如中國新左派之類的廣義群組的一部分。我且稱呼這些知識分子為中國左派民族主義者。
中國藝評人暨前學者榮劍最近發表了一篇文章,批評中國其中一位最著名的左派民族主義者汪暉,引起了一時轟動。榮氏將汪氏比作納粹黨成員及支持者的德國哲學家馬丁·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榮氏認為,汪氏主張諸如列寧和毛澤東等具備超凡魅力的政治領導的二十世紀革命人物的重要性,並捍衛了日益增長的習近平個人崇拜。這一論調讓人想起海德格對元首希特拉的阿諛奉承,將之高捧為其法西斯主義本體論中的核心造神人物。
反新自由主義與民主
中國左派民族主義者信奉一種區分中國與西方國家的本質差異。這種差異的根源被視為「中國文明」與「西方文明」之間的分別;又或者以現代一點的說法,如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分別。對於這些思想家而言,這種差異本質在於中國語境中的政黨和國家首要地位以及西方語境中的自由市場或民主政制主導兩者之間存在的衝突。因為施密特推祟民族國家概念,這正正是中國左派民族主義者會傾向施密特這種人物的原因。的確,只要中國民族主義者繼續以二元的方式設想當前的世界秩序(這種世界秩序在冷戰時期已經存在,且於今天以中美地緣政治中再生),施密特將政治活動簡化為「敵友」之分,對中國民族主義者有其吸引力。放寬對施密特思想的理解,將容許他們尊崇國家至高無上的地位,且合理化加強邊界以抵抗外來威脅的欲望。
過去幾十年,中國左派民族主義者藉鑑了歐美左派學術界的新馬克思主義和後結構主義的方法,將中國於上世紀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轉向自由市場,與西方左派對新自由主義的分析相扣連。在這種脈絡下,諸如大衛·哈維(David Harvey)和娜歐米·克萊因(Naomi Klein)之類的西方理論家傾向將中國新左派視為同道中人,這關係可從他們對新自由主義秩序的基礎批判論著如《新自由主義簡史(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和《震撼主義:災難經濟的興起(The Shock Doctrine)》中大量引用汪暉中看出端倪。然而也是在這段期間,中國左派民族主義者開始對施密特表現興趣。
汪氏亦一直為中共辯護,指中共儘管並未實質實行民主,卻實施了表達民主共識的思想。其中一個例子是他對「群眾路線」的重視,而這是毛澤東在制定政策時用來徵詢群眾的一種策略。汪氏辯說,這些實踐是西方模式未能實現的民主表達:「群眾路線人民戰爭的基本策略,它是政黨的政策,也是重構政黨的⋯⋯條件下的政黨及其群眾路線創造了階級的自我表達,從而也創造了政治性的階級。」 2 汪氏亦為國家無法主張民主作出辯駁:「如果一個國家的政治體系具有強大的能力來應對問題,則表明該社會包含著民主的要素和潛力。但是因為我們的民主理論太過集中關注政治形式,因而忽略了這些實質性潛力。」 3
捍衛黨國
人常說,一部反應靈敏的國家機器不一定民主,但也許是有效率的。有些時候,連假裝民主的功夫都省掉的威權國家會通過聲稱它們的政制比民主制度更有效率來證明其統治的正當性。
的而且確在歷史上,不少政黨和國家都聲稱為人民發聲,實際上卻只代表了特定的利益集團。許多人正是如此批評當代中國黨國:它只是一個機構,其目的只是為了保護少數強大、有政治影響力的創黨家族,而不是一個屬於中國人民的機構。正如尼采所說:「國家是最寒冷的怪物,冷冷地說著謊,從它嘴裡爬出這樣一句話:『我,國家,就是人民。』」
汪暉在黨與國家之間作出了區分,認為黨與國家「不完全」相同是中國政治制度的優勢,而在鄧小平時期,兩者日益衰落,這優勢就消失了。 即使如此,汪氏仍試圖恢復黨國雙方。
這基本就是簡化的國家辯解書;他將對國家的評價與西方政治模式相提並論,認為相對於中國政治體系中國家較強勢的地位,西方政治模式主要缺點是國家的角色較弱。這種對黨國的辯護試圖破壞人民、黨和國家之間的區別:汪氏經常歸順於群眾路線的同時,也認為黨國可以代表某種盧梭式的公共意志。
當然,這裡的基本分析單位是國家(或者在中國情況下是政黨國家)。由於無法討論沒有國家的人,汪氏自然對自決的原則作出負面評價。特別是,他不認為無國家的自決訴求值得認真考慮。正是基於這種分析角度,汪氏同時廣泛地反對中國周邊地區的自決。他認為在中國治下,獨立的藏族和維吾爾族身份將隨著歷史而消失。他對香港和台灣身份的看法是一致的;根據汪氏,這些身份是最近才出現的,而且也可能突然崩潰。
如此看來, 如胡鞍鋼等熟悉中國左派民族主義的人士甚至直接主張中國成為一個民族國家,也就不足為奇。胡氏在2012年發表的一篇論文中寫道:「任何國家的長期和平與穩定都建基於建立具有統一種族(國家種族)的制度之上,以加強國家種族身份並稀釋其他族群身份。」期後胡氏的論點被用以支持鼓勵漢族與維吾爾族通婚的做法以淡化族群身份,從而使汪氏對身份的觀點得到合乎邏輯的結論。
「革命者人格」
汪氏對黨國的強悍辯護,最近轉向為習近平「革命者人格」辯解,這實際上卻與他的早期論說背道而馳。過去汪氏通過辯稱群眾路線是一種有效的民主決策系統來合理化黨國體系,最近則發聲支持領導地位取代所領導政黨的個別領導人物。他稱這領導人物為「革命者人格」。
在汪氏最近於2019冠狀病毒全球大流行期間撰寫的文章〈革命者人格與勝利的哲學--紀念列寧誕辰150週年〉中,他指出:「以神話方式完成其使命的個人既是政黨的領袖,又不能等同於政黨體制本身:在許多歷史關頭,列寧、毛澤東等革命領袖常常與自己的政黨及其主導路線處於對立的狀態,他們通過持久的、有時是殘酷的理論和政治鬥爭,才獲得黨內的領導權。」因此,汪氏再指出:「在工人運動、階級性政黨和社會主義國家衰落的背景下,重新探討革命者人格(尤其是革命領袖的人格)在20世紀政治中的作用,對於推動當代世界的重新政治化而言,不是沒有意義。」在這裡,政治領導人的例外主義觀點似乎壓倒了他對國家計劃的支持:「革命者人格具有一種獨特力量,在社會條件、政治條件尚不具備的狀況下,能夠以巨大的能量推動革命的進程。」
因此,對於榮劍來說,汪氏的「革命者人格」讓他聯想起海德格對元首的看法,也許並不足為奇。在這一點上,我們可以將「革命者人格」與彌賽亞主義脈絡中的其他思想人物進行比較,例如黑格爾的世界精神或尼采的超人論。但是,汪氏在習近平捨棄旨在防止另一位如毛澤東或鄧小平模式權力不受約束的領導人崛起保障措施之時,書寫「革命者人格」的重要性,必然也跟習近平政治權力崛起有關。即使汪氏並沒有公開推崇人格崇拜,他對「革命者人格」重要性的評估也佐證了習近平的祟高地位。
偽裝成國際主義的擴張主義
汪暉以及其他中國新左派人物的論說已經明確表明中國左派民族主義者並無意在無國家人士之間建立團結,而只是渴望在中西之間的大國競爭中獲勝。這是一種偏狹的觀點,危險地否定了面對全球資本作為一種集結力量,只有國際主義的工人運動才能夠與之抗衡的邏輯。反之,汪氏視推動歷史進程的主體為具有超凡魅力的領袖人物所領導的黨國。
根據這些中國左派民族主義者的觀點,西方代表資本主義,只有中國國家政權能與之抗衡。按照這種邏輯,中國的社會主義僅與國家權力緊扣,並完全被構想為國家權力的行使,而幾乎沒有提及馬克思所描述的「國家消亡」後的無階級社會。他只不過以「社會主義」的名字代表一種民族繁榮的有限視野,並提不出任何全球後資本主義的未來。
這種關於國家權力和後資本主義未來的辯論基本上並不新鮮,目前所涉及的許多問題在蘇聯成立初期以及第三國際成立時也曾為爭論焦點。但是,就史太林領導下的蘇聯而言,聲稱推進一個國際性社會主義計劃的第三國際實際上只是促進蘇聯國家利益的部署。(榮劍指出,汪氏讚許以列寧而非史太林為主的「革命者人格」,迴避了公然主張史太林主義的人格祟拜復興。)
習近平與史太林蘇聯的類比,可延伸到非西方帝國主義計劃和當今帝國主義的形成。上世紀三十年代,日本帝國建立了「大東亞共榮圈」,以促進東亞國家之間的文化和經濟統一。當時的日本知識分子為之護航,聲稱這是一個可以克服西方現代性的世界歷史項目,而西方現代性被視為破壞了日本「傳統」的具體概念。1942年在東京舉行的「超克現代(近代の超克)」會議是中國左派民族主義者臭名昭著的試金石,但他們似乎仍然故意無視日本帝國知識份子為國家作出的辯解與他們自己的政治計劃的相似之處。4 正如中國對日本強烈敵意所顯示 ,其他團體幾乎沒有一個認為日本帝國主義是解放性的。偽裝成國際主義的中國國家計劃也一樣。
從這個意義上講,許多中國左派民族主義者的「左派觀點」實際上植根於資本主義國家主義,以作為社會生產資料的根本性重整。結果,大模斯樣的國家主義計劃諸如漠視中國周邊地區的自決抗爭、為內部殖民主義以及中國的地緣政治擴張辯護,都被錯誤地歸納為左派國際主義的倡議。
相對地,美國的帝國主義並自我正當化為一種全球範圍內傳播自由和民主的使命。在這方面,中國左派民族主義者以一種類近西方另類右翼的角度來構想當代世界秩序,後者同樣將中美衝突視為文明衝突。因此,當前的全球資本危機激起了中美之間的平行應對,兩者均著重於加強和維持其邊界。在中國,這很明顯地體現在強調西藏或新疆內部邊界的治安,以及對香港和台灣等外部邊界的操控。對於美國, 這顯現為日益激烈的反移民言論和國內針對少數族群的暴力。因此,中美衝突是現代民族國家之間的衝突,兩者共同擁有帝國主義的民族主義行為,儘管雙方的民族主義者在意識形態上都無法接受這種趨同實踐。
二十世紀的歷史充滿了帝國工程的殘骸。前殖民國家或因不平衡發展而處於不利位置的國家已著手推行民族主義自強工程,導致一種取代主要西方強國的試圖。儘管反對西方霸權是至關重要的一項,但許多此類工程最終都以西方一直佔據的全球霸權地位為目標,而不是去完全擺脫大國競爭的循環。這就是我們目前在中國所看到的,也是中國左派民族主義者依靠極右計劃和法西斯主義理想所大力擁護的。不反對這些思想的話,我們可以預期,現代帝國之間的這場衝突也將以類似昔日帝國主義的方式行進。
腳註
- 在此「新疆」指新疆維吾爾自治區(XUAR,又稱「新疆(Xinjiang)」、「西北(Northwest China)」、「東突厥斯坦(East Turkestan)」、「維吾爾亞(Uighuria)」、「伊犁(Ghulja)」、「塔爾巴蓋(Tarbagai)」、「阿勒泰(Altay)」、「宗喀則和阿勒泰沙爾(Dzungarstan and Altishahr)」或「宗喀則和塔里木盆地地區(Dzungaria and the Tarim Basin Region)」,以下簡稱「新疆」)。追溯詞源,新疆是一個備受爭議的專有名詞。乾隆皇帝最早於十八世紀使用該詞,並於十九世紀末左宗棠重新佔領該地區後正式將其命名為「新疆」。在普通話中,它的意思是「新的領土」、「新的邊境」、「新的邊疆」。
- Wang Hui, China’s Twentieth Century: Revolution, Retreat and the Road to Equality, ed. Saul Thomas, London: Verso Books, .140.
- Ibid p.160
- Harry D. Harootunian, Overcome by Modernity: History, Culture, and Community in Interwar Japa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