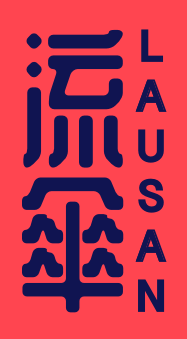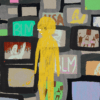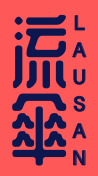本文原刊登於無政府主義思想平台《Crimethinc》;流傘獲授權翻譯。詳情請聯絡流傘義務翻譯團隊。
譯者:Mary, NN, Ran
響應冠狀病毒全球大流行造成的經濟困境,全球各地均有抗租的呼籲。過去十年,房地產價格飛漲,仕紳化摧毀了無數社區。早在全球瘟疫引發這個問題很久之前,住屋價格已是無法持續。
然而,我們如何因應經濟衰落本身抗租呢?當我們想到抗租時,通常會想到一種針對個別房東、向其提出個別要求的戰略模型。實際上,如以下文所述,該策略在以前已被有效用於更廣泛的基礎上。在一場危機中,不管他們願意與否,當大部份的人均無力支付水電煤或是房屋費用,最重要的是建立一個能夠捍衛所有無力者的網絡。在接下來的幾個月,我們必須建立一種團結的力量來面對所有試圖懲罰、驅逐,或迫遷租客的房東。
下文摘錄自《Editorial Segadores》和《Col·lectiu Bauma》的西班牙語版本,原文在本年三月底於加泰隆尼亞發表。文章作者們回顧了一個多世紀以來世界各地的抗租案例,以期找出使它們成功或失敗的原因,以便評估現今是否發動全球抗租的最佳時機。
現在是抗租的時機嗎?
「之所以有一群突然對抗租感興趣,但沒有正統組織經驗的人出現,並不代表一種自發主義或極左主義,也不代表以前參與過正統組織的人某些道德上的失敗。這標誌了一個事實,即不斷變化的物質條件將這一策略結合了(一)生存,及(二)新增的籌碼。新的條件意味著新的組織方式,而不是只在跺腳並堅持舊有方式。」-Joshua Clover
「但是我不可能一次過把他們全都驅逐!」
-顯然,一位房東在收到「他的」物業裡的三十二位租戶各自的來信宣布抗租的打算後,通過互聯網論壇尋求建議。2020年3月25日,美國德薩斯州侯斯頓。
這是非常的時代。春天到來,伴隨著冠狀病毒以驚人的速度在全球擴散,國家的極權反應使我們陷入新的局勢。在警察濫權的同時,許多人失業,更多的人不知道能否熬到月底。在這種情況下,抗議聲音此起彼落,抗租的想法也越來越受到關注。《Editorial Segadores》和《Col·lectiu Bauma》希望調查這種抗租行動,回顧一些過去的著名案例,並預想在病毒時代的抗租行動會以甚麼模樣呈現。我們希望這些思考能幫助有意制定戰略和採取行動的人,通過批判性思維和直接行動,對應禁閉和限制。

抗租是甚麼?它如何運作?
當一群租戶集體決定停止支付租金的時候,就是抗租。他們可能有相同的房東,或居住在相同的社區。抗租也可能在另一場運動當中發生,是更大的鬥爭中的一小部分,也可能是反抗仕紳化、反抗惡劣生活條件、反抗廣義上的貧困、反抗資本主義本身的主要軸心行動。
要取得成功,抗租需要三個元素:
一、共同的不滿。開始時,即使鄰居們未有統一他們的訴求,必要的一點是,他們當中多數人以或多或少相同的方式理解現狀:即是這是令人髮指的或無法忍受的、他們正冒著失去住屋的風險、他們不相信現有的渠道能帶來公義。
二、外展。就像我們將於下文看到的那樣,絕大部分的抗租行動都是從一小部分人發起的,並且從那裡開始擴大。因此,他們需要傳播行動號召、傳達訴求,並尋求支持和團結的渠道。在許多情況下,抗租者只有在三分之一的租戶參與行動時才能取得勝利,但要達到這數字並令抗租擴散的威脅使人信服,就必須進行充分的外展宣傳。
三、支援。抗租者需要支援。他們需要面對法院程序時的法律支援、失去家園的人需要住屋支援、對抗驅逐時肢體上的支援,以及面對大規模鎮壓時的戰略支援。在許多情況下,尤其是在大型抗議行動中,抗租的租戶都能在自己的行列中找到所需的支援,互相支持,並建立生存所需的架構。其他情況下,抗租者會向現有組織尋求支援。但是抗租行動的主動權總是來自敢於發起抗租的租戶。
現在讓我們看看這三個主要元素怎樣在歷史中重大的抗租行動中實現。
1901年:愛爾蘭羅斯康芒郡De Freyne Estate
1901年,隸屬愛爾蘭羅斯康芒郡(Roscommon County)大地主De Freyne男爵的農場爆發了拒付租金行動。過去幾十年,該地區的租戶通過與抵抗英國殖民主義和大饑荒的影響相關的運動,鞏固了對抗大地主的組織能力。這些運動並未在羅斯康芒郡紮根,但當地居民肯定對這種實踐有所了解,並且參加了一些半非法的抗命行為。這些抗命行為一直是農村租戶生活的一部分(群眾集會、以身體對抗驅逐、破壞、縱火等)。
二十世紀初,當地居民由一個處理農業和經濟問題的民族主義組織「統一愛爾蘭聯盟(United Irish League,簡稱UIL)」所領導。當住民開始自主抗租,他們馬上連結上當地的UIL,而其他團體則與他們聯繫以支持他們的抗租行動。同時,UIL的高層領導表現得模棱兩可,有時提供支持,其他時候則試圖將抗租定性為一個一次性的、而不完全反對租賃和財產的概念的獨立行動,因為當時UIL的領導仍在嘗試遊說部分資產階級加入他們。
抗租的直接起因包括一場摧毀了大部分收成,並抬高了飼料價格的暴雨、De Freyne男爵拒絕降低租金價格、債台高築及眾多家庭被驅逐,以及土地所有權方面長期不公正的歷史,加上近期鄰近莊園的一些居民被允許購買土地,而De Freyne的租戶卻被迫繼續像農奴一樣生活,這些因素加劇了事態發展。
抗租行動於1901年11月開始。起初,De Freyne的許多租戶都是秘密地和非正式地組織起來的,因為雖然UIL支持租戶,但並沒有主動採取行動。抗租蔓延到其他莊園,持續超過一年。超過九成的De Freyne土地租戶參加了行動。他們通過修建路障、向警察投擲石塊,以及非法建造新住宅來對抗驅逐。
這成了全國性的醜聞。1903年,英國議會被迫推行廣泛的土地改革,從而終結了佃農制度。
Daphne Dyer Wolf著:〈Two Windows: The Tenants of the De Freyne Rent Strike 1901-1903〉〔兩個窗口:De Freyne抗租行動中的租戶,1901年-1903年〕(博士學位論文)。德魯大學,2019年。
1907年:布宜諾斯艾利斯和羅薩里奧「掃帚抗租行動」
1907年8月,布宜諾斯艾利斯市政府下令下一年實行增稅。房東們隨即把租金上調。貧困地區的生活條件本身已很淒慘。前一年,阿根廷地區工人聯會(Federación Obrera Regional Argentina,簡稱FORA)曾發動租金下調的運動。
9月13日,同一街區裡的一百三十七戶住宅的婦女發起了自發抗租行動。她們趕跑了試圖驅逐租戶的律師、官員、法官和警察。到了月底,在由FORA組織的動員和架構協助下而成的、由婦女組成的委員會領導下,超過十萬名租戶參與了抗租。他們要求租金下調三成;當警察到場驅逐租戶時,他們投擲彈石並埋身肉搏,竭盡所能抵抗。
抗租蔓延到其他城市,包括羅薩里奧(Rosario)和布蘭卡港(Bahía Blanca),吸引了各種勞工、無政府主義者和社會主義組織的支持,其中主要就是FORA。警方的鎮壓非常激烈,曾謀殺了一位年輕無政府主義者。最後,儘管抗租者阻止了驅逐行動,但並未能成功迫使房東下調租金成本。 經過三個月的激戰,許多組織者(如Virginia Bolten)被官方以《居住法》名義驅逐出境之後,這場抗爭因而失去了動力。
La Huelga de las Escobas 〔掃帚抗租〕
Anarquistas: la huelga de lxs inquilinxs de 1907 〔無政府主義者們:1907年的租戶抗租〕
1907年:紐約曼哈頓抗租行動
在1905年至1907年之間,紐約市的租金上漲了33%。城市不斷擴張,前來工廠、建築和港口工作的貧窮移民人口膨脹。無政府主義和社會主義活動也在激增。秋天,房東們再度宣布上調租金。二十歲的工人、猶太移民與社會主義者Pauline Newman便採取行動,說服了其他四百名年輕女工支持抗租的呼籲。到十二月底,她們已經說服了數千個家庭;在新年,一萬戶家庭停止繳租,並要求減少18-20%的租金。幾星期內,約二百戶家庭的房租被減低了。這事件成為往後數年的鄰里鬥爭與及後國家實施租金管制的開端。
The New York City Rent Strike, 1907-8〔紐約市抗租行動,1907至1908年〕
1915年:格拉斯哥,「Barbour太太的軍隊」
1915年前幾年,隨著戰時工業化和農村家庭移民湧入,蘇格蘭格拉斯哥市迅速發展。擁有物業的資產階級推測住屋需求,固意空置11%的住屋,不為新建築提供資金,而工人階級則居住在越來越擁擠和日益惡化的房屋中。蘇格蘭住屋協會和各種工會花費多年時間執行住屋和租賃領域的法制改革;他們贏得一些新法律,但總括來說,情況持續惡化。此外,一次大戰令食品價格不斷上漲,許多男人都出征國外。房東們利用了這優勢,認為在男人們都離開了的情況下剝削貧困家庭會更容易。1913年8月至9月期間,格拉斯哥發生了484次驅逐。1915年1月至3月期間,高達6,441次。
當工人階級都被苦難、剝削和大屠殺逼害時,格拉斯哥的房東們卻從中看到了一個好機會。在1915年2月,他們宣布所有租金上調25%。在2月16日,加文區(Govan)南部的所有貧窮女性立刻召開了一個群眾大會。出席的有來自格拉斯高女性住屋協會(Glasgow Women’s Housing Association,簡稱GWHA)的組織者。這個組織在前一年形成,但還沒有很大號召力。在大會上,她們成立了隸屬於GWHA的加文區南部女性住屋協會。她們決定了繼續支付原來的租金,不付上調的費用。這個行動傳遍了整個社區。
女性們寧可建立自治組織,也沒有加入傳統組織。很大程度上,組織背後的強大力量就是貧窮女性在日常的看顧活動中建立的團結網絡。
GWHA在5月1日召集遊行,引來了兩萬人參與。6月,加南區的女性成功取消了租金上調,而運動從那裡亦開始擴大。在10月,整個城市有多於三萬人參與抗租運動。她們後來從加南區工人Mary Barbour得名,被稱為Barbour太太的軍隊(Mrs. Barbour’s Army)。在散佈和維持抗租行動的過程中,她們組織遊行、抗議、保護租客不被驅逐,與警察不斷交手。工會威脅在軍械廠罷工;在年底,他們成功暫停所有對罷工者的懲罰行為,贏得了凍結租金、維持戰前價格,以及落成英國第一套租金控制的法律的成果──對達到在不久以後引入的社區住屋邁進重大的一步。
運動一開始的時候,就已經贏得左翼政黨和其他現有關注房屋的組織的支持,例如跟蘇格蘭社會主義黨有聯繫的房屋協會聯會。但必須強調的是,女性們寧可建立自治組織,也沒有加入傳統組織。她們之中有些會跟GWAHA第一位主席Mary Burns Laird一樣,與政黨一起組織(在Laird的情況就是工黨),有些則像Barbour太太一樣不隸屬任何政黨,創建屬於自己的鬥爭道路。無論如何,GWHA的活動跟傳統左翼政治相差很遠:她們在自己的廚房、洗衣池,和街上舉行會議。很大程度上,組織背後的強大力量就是貧窮女性在日常的看顧活動中建立的團結網絡。
1915年: 格拉斯高抗租行動
Brenda Grant, 「一場女性的鬥爭:1915年格拉斯高抗租行動」(2018)
1931年:巴塞羅納,經濟防禦委員會
1931年,巴塞羅納剛剛脫離專政。所有人都急切地等待民主將帶來的進步,然而卻没有等到。那時候巴塞羅納已經變成了歐洲最昂貴的城市,租金達到薪金的30%-40%。(今天的數據挺相似,或者更差。但那時候,歐洲的城市平均都是15%)居住情況十分惡劣。很多沒能力負擔租金的人只能去一些讓工廠工人輪班的時候休息的睡房(Casas de Dormir);這些房間很多時候連床都沒有,只有讓工人放鬆手臂的繩子。
4月,一場抗租行動爆發,其中的參與者要求租金下調40%。有45,000到100,000來自城市各方的人參與這個行動,持續到12月。由全國工人聯會(Confederación Nacional del Trabajo,簡稱CNT)建築工會成立的經濟防禦委員會(Comité de Defensa Económica,簡稱CDE),在抗租行動上的擴展和協調上扮演重要的角色。
與許多其他抗租行動一樣,這個行動的特點就是參與行動的鄰里團結精神。他們一同建立路障,一同抵抗驅逐。當他們成功了,就在街上慶祝;失敗了,就回去被驅逐的房屋裡面慶祝。早上來關掉水源電源的工人晚上又會回來重新將它打開。當然他們跟CNT是有聯繫的。有時候,因為厭倦又要回到重新佔領的房屋,警察會把傢俱銷毀或扔出窗外。其他策略包括我們今天認識的esrache,即是在房東的住宅外面抗議。
顯然地,抗租行動不是無中生有:它建基於社區自治的傳統,紮根於多元的關係網絡以及由鄰舍和親屬關係所孕育的連結。抗租運動也跟CNT從一次世界大戰培養的激進文化有密切的關係。
「CDE的組織者Santiago Bilbao,把抗租行動視為一個重要的經濟互助活動,可以讓被剝削者抵銷市場力量,重新掌控自己的日常生活。CDE給工人的忠告是:『吃好。沒錢的話,不要繳付租金!』CDE也要求失業人士免交租金。雖然抗租行動是通過CDE籌劃的群眾大會往外擴展,但這場運動的真正起源是自比任何組織都重要的街頭上。」– Barcelona (1931), Huelga de Inquilinos
「抗租行動源於巴塞羅內塔(Barceloneta)一帶,該社區有一種活躍的社會意識,既來自生活艱苦的漁民,也來自於在金屬工業中首當其衝的公司Maquinista Terrestre y Marítima的工人們。在這個臨近地中海的鄰舎裡,漁民的房屋仍被稱作“火柴盒”,因此,不滿從此衍生一點也不稀奇。這些十五或二十平方米的房屋裡住了整個家庭,有時還會有寄宿者,例如最近從村裡來的親戚。 […] 正是CNT的Sindicato Único de la Construcción動員勞動家庭的不滿情緒,逐點逐點的使之漸蔓延到城市邊緣,而每個鄰舎的行動都有其個別特徵、自身特質和抗爭的方法。」–Aisa Pàmpols, Manel著,(2014年):〈La huelga de alquileres y el comité de defensa económica〉〔抗租與經濟防禦委員會〕,巴塞隆拿,1931年4月。
Sindicato de la Construcción de la CNT。巴塞隆拿:El Lokal。
抗租行動在統治者Oriol Anguera de Sojo和財產所有者協會主席Joan Pich i Son領軍的嚴厲鎮壓下結束,後者同時剿滅了1934年10月的暴動。當新的民主共和國調出整隊軍隊,包括警察、民警(Guardia Civil),和新編的準軍事部隊(Guardia de Asalto);他們看起來跟以往的獨裁政權大同小異。其實施的《共和國國防法》是一項限制言論自由法,為獨裁壓制提供了全權通行證。有的人作為「政府囚犯」被囚禁,而CDE亦被宣佈為犯罪組織。
儘管如此,持續的抗議仍在為即將發生的革命點燃餘燼。
大部分抗租的原始記錄在戰爭中被銷毁,也許是因為當局擔心後人會效仿這個無產階級抗爭的例子。因此,我們失去了大部分在抗租行動中發揮核心作用的婦女們的聲音。雖然CNT作為行動的中心角色的重要性是不容置疑的,然而在史學中,正規組織總是比非正式組織和空間獲得更高度重視。但是每個社區的抗租策略都不同的這一事實告訴我們,抗租行動並無中心大台統領,而是首先取決於發動抗租的人們。
Barcelona (1931), Huelga de Inquilinos 〔巴塞隆拿(1931年),租戶抗租〕
Aisa Pàmpols, Manel著,(2014年):〈La huelga de alquileres y el comité de defensa económica〉〔抗租與經濟防禦委員會〕,巴塞隆拿,1931年4月。Sindicato de la Construcción de la CNT。巴塞隆拿:El Lokal。
1959-1960年:倫敦聖潘克拉斯
位於倫敦裡的聖潘克拉斯是一個工人階級佔大多數的社區,有大約8,000人居住在公共住宅。
在1958年,該地區投票通過了上調公共房屋的房租。在次年的7月底,在保守黨贏得地區選舉後房租再次上調:這次比以往更誇張(100%-200%),還趕走了所有工會(以前該地區的工人都必須是會員)。直到那時,四周都很少鄰里組織,但是在8月初,就有一個地區的鄰里成立了一個協會。到8月底,25個相似的租戶協會相繼成立,而每個協會都在新成立的聯合租戶協會(United Tenants Association,簡稱UTA)的中央委員會中均有代表成員。秘書Don Cook就曾經擔任過少數在1959年前成立的其中一個(小型)租戶協會的秘書。
從一開始,大部分的成員都支持直接行動和抗租行動,但是工黨因為想利用租戶的要求來擊敗保守黨及重新控制地區,所以阻止了他們。
1959年9月1日,舉行了一個四千人參與的遊行和會議。參與者採取了不同的主張,包括拒絕填寫用來評估每個家庭新租金的所需文件、呼籲大眾團結起來、承諾保護任何面臨驅逐的家庭,以及要求工會的支持。接下來的幾個月,租戶繼續舉行示威。在工會的支持下,他們在每一個街區成立委員會,每週舉行超過200人參與的代表大會。他們出版了三期的每週通訊,將來自領導層的訊息傳播給眾會員。年底的時候,UTA已經囊括了35個租戶協會。
女性們晚上都在地區議員的家外抗議。每個議員每個星期至少會被針對兩次,也因此睡得很少。在少數關於這場抗租運動的故事之中,有一個參與者(Dave Burn)承認女性「構成了運動的骨幹。她們每天都保持著動力,互相支持。」然而,Burn的故事大部分都聚焦於正式的、男性代表主導的組織。
租金上調原定於1960年1月4日生效。起初,多達80%的公共房屋租戶沒有支付上調的費用,只支付原來的租金。但是經過多番的威脅,加上地區開始啟動驅逐程序,抗租運動的參與下降到只有四分之一,即是大概2,000個租戶。2月,工黨忠告UTA取消抗租行動,好讓他們可以跟保守黨談判。UTA拒絕了:因為如果沒有抗租行動,他們更毫無自衛能力,況且已經有幾個家庭陷於驅逐的程序之中。
抗租行動不是無中生有:它建基於社區自治的傳統,紮根於多元的關係網絡以及由鄰舍和親屬關係所孕育的連結。
UTA為了要集中力量,減少同時間對抗眾多驅逐,籌劃了一個集體付款行動來應付大部分的欠租金額。第一輪的判決在8月下旬安排了三個驅逐。租戶開始組織他們的防禦,堅決不能讓任何驅逐在公共房屋裡發生。在7月,運動進行的中途,UTA的領導跟地區議員會面,但因為保守黨拒絕了解租戶的問題,導致談判失敗。從那一刻起,UTA就啟動了一個徹底的抗租行動。在8月中,他們額外收到250個驅逐令。
到了8月28日,租戶已經建起了龐大的路障;他們準備好能夠警戒整個社區的糾察和警報系統,令工人能夠及時罷工去捍衛人們的房屋。截至8月14日,驅逐令已經上升到514個。工黨和共產黨都紛紛懼怕愈趨緊張的局勢,呼籲終止抗租行動,但是已經太遲了。
9月22日的早上,800個警察向人民發動攻擊。一個警察在隨後兩小時的爭鬥中嚴重受傷。警察成功驅逐了兩所房屋,但是在一個街區,衝突一直持續到正午。大約300個當地工人前來幫忙保衛抗租的行動,但工會並沒有提供任何支持。下午,1,000個警察攻擊了一個有14,000租戶參與的遊行。衝突一直延續。
地區議會的領導示意他準備好會見UTA的代表。第二天,內政部長宣布禁止所有示威和集會。
因為暴動所引致的政治醜聞,工黨離棄了租戶而開始譴責「煽動者」和「激進份子」。他們指稱有外部勢力參與了抗租運動,而堅持要用對話來解決這個衝突(儘管在這一年間,地區裡的保守派近乎每一次都拒絕對話)。同時,在談判以後,保守派只批准了微小的租金下調。
受到左右兩派的攻擊,而且每天都面對新驅逐的威脅,UTA決定改變策略來避免更多的驅逐。他們繳付了那些驅逐風險最高的鄰居的欠租金額,並決定幫助工黨在臨近的選舉中踢走保守黨。1961年5月,工黨贏得地區議會的控制權,51個議員比19。幾位UTA的代表加入了他們的組織,而他們選舉平台的主要議題就是租金改革。
租戶們等待著公共房屋的租金改革,但一天又一天過去了,卻一直沒有等到。那兩個被驅逐的租戶找到新的房屋了,但是過了幾個月,工黨議員宣布租金改革沒有可能。抗租行動失敗了。
1970年代:意大利「自我削减」行動
1960和1970年代的意大利是勞工和住屋問題日益嚴重的時代,也是人們夢想並勇於追求一個免於剝削的世界的年代。1974年,仰仗着共產黨的中立取態,工業和金融業界裡最具遠見的技術專家引入了Carli計劃。該計劃旨在增加勞工剝削及減少公共支出。
在1960年代,意大利一個強大的自治工人運動影響了社區自治運動的興起。這些自治組織由自發組織的鄰里委員會組成,其中婦女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著眼於人們實際、直接的生計,這些委員會組織了「自我削減」行動:租戶和鄰居自行決定下調服務價格,例如僅支付五成的水電費用。
在都靈,運動於1974年夏天獲得了相當動力。當公共交通公司決定提高票價時,他們即時作出反應。參與者自發在各地點封鎖公共汽車、分發小冊子,並派代表進城。從此,最激進的工會開始組織一個大眾化的回應方式:他們自己打印公車車票,由義工在公共汽車上分發,收取加價前的票價。透過集體的力量,他們迫使公司接受現狀。
電費的自我削減行動分為兩個階段迅速傳播:首先,在工廠和附近地區收集承諾參與自我削減行動的簽名,然後,利用公用事業工會洩漏出來的有關賬單於何時何地郵寄的訊息,在郵局外設置糾察線。糾察員會發放有關如何參與自我削减行動的資訊。幾星期後,都靈和皮埃蒙特地區的十五萬個家庭參與了行動。
每個社區的抗租策略都不同的這一事實告訴我們,抗租行動並無中心大台統領,而是首先取決於發動抗租的人們。
都靈的自我削減行動相對強大,因為地區工會是自治的,獨立於阻止所有針對價格上漲的直接行動倡議並被共產黨控制的全國委員會。因此,在都靈,工會可以向自發和鄰里委員會的倡議提供力量和支援。但在米蘭等城市,工會並不支持這些倡議,或者像拿坡里那樣,本身已不存在強大的工會。在某些城市,如帕勒莫,學生和年輕人通過非法行為實踐自我削減。
運動擴展到租金的自我削減,目的是使租金不超過家庭工資的一成,並為此採取了各種策略,諸如小團體的努力到由更激進的工會支持的居委會等各種舉措。70代上半葉,參與者佔據了20,000戶房屋,短期內擺脫了租金的商業邏輯。在羅馬、米蘭和都靈也發生了抗租。
女權運動是其中一個主要力量。在這語境下,婦女們發展了有關的三大剥削──來自上司、丈夫和國家──與再生產勞動的理論;這些理論在時至今日的抗爭仍至關重要。
Autoreduction movements in Turin, 1974 〔都靈的自我削減行動,1974年〕
Mapping the Terrain of Struggle: Autonomous Movements in 1970s Italy〔繪畫抗爭地圖:1970年代意大利的自治運動〕
1980年代:南非,索維托城鎮
索維托是約翰尼斯堡一個人口密度很高的市區。在1980年代,它有250萬居民。在種族隔離制度的最後幾十年,索維托的居民經歷了極端貧困和社會排斥。這引發了1976年的索維托起義,帶來了一系列強大的抗議、罷工行動,以及一場導致數十個人死亡的警暴鎮壓。該地區的物質條件開始逐漸提高,而這都該歸功於居民持續的抗爭。
那裡的住屋情況十分惡劣。所有房屋的質量都很差、不衛生,並且雜亂無章。租金和服務費的費用已經佔了居民一般收入的三分之一,更何況失業率不斷飆升。1986年6月1日,當上調租金的計畫被傳開,上千名索維托居民停止向索維托議會繳付租金和服務費。議會嘗試用驅逐終止抗租行動,但是鄰居們都以武力抵抗。八月底,警察向一群抵抗驅逐的群眾開槍,殺了超過20個人。因為群眾憤怒情緒加劇,政權終止了驅逐。
1988年初,政權用宣布進入緊急狀態來壓制全國各地興起的黑人抵抗運動。他們唯一不能消滅的焦點就是索維托的抗租行動。在年中,抗租行動仍然持續,而政權為了施壓,切斷了幾乎整個地區的電力供應。
新聞聲稱抗租行動並不實際,只是因年輕激進分子的武力才得以維持。但是現實卻不一樣:儘管30個月的緊急狀態暫停了大部分反對種族隔離制度的運動,絕大多數的居民都繼續支持抗租行動。最後,政權承認自己對狀況已完全失去控制。在1989年12月,他們取消了所有欠租的金額,給政府帶來了超過1億元的損失,並決定性地終止驅逐,暫停所有未經由居民協商的租金。此外,在超過5萬個案件中,政府直接將擁有權轉讓給了租戶。
在這些抗租行動以前,反對種族隔離制度運動曾經使用抗租行動作為對抗白人政府的抗爭策略,所以全部人民都對此非常熟悉,這個運動的動員和組織都擴展了對於團結的實踐。然而,1984年9月在萊哥亞開始的第一個大型抗租行動是鄰里對於租金上調的即時反應,最熱烈參與的組織就是瓦爾當地的瓦爾公民協會(Vaal Civic Association)。這可能就是非洲國民大會(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簡稱ANC) 和其他組織隨後開始使用抗租行動策略的來源。
同樣地,索維托的抗租行動之所以從自己社區裡開展,是因為它在回應當前的實際環境以及生存的逼切性。它是非正式鄰里網絡作為組織抗租行動關鍵的一個經典例子,而正式的體系則因應抗租行動開始後的需要而相繼成立。雖然女性被一些正式的組織排斥,但是她們在構建和維持重要的鄰里網絡上擔當一個關鍵的角色。
抗租行動給予南非黑人一個強大的武器
南非黑人計畫群眾行動:抵制商店與抗租行動都是策略的一部分
武裝的人民, 1984年-1990年
索維托市議會放棄鎮壓抗租運動的計畫
2017年:洛杉磯,博伊爾高地 (Boyle Heights Mariachis)
一個房東因企圖通過種族歧視進行仕紳化,把少數在洛杉磯波伊爾高地社區Mariachi Plaza旁邊的大廈單位租金調高了60-80%。一半的租戶立刻成立了一個聯盟,其中包括一些沒有直接被租金上調影響的租戶,要求跟房東對話。當房東嘗試跟他們個別地聯絡,聯盟就發動了抗租行動。隨後,洛杉磯租戶聯盟 (Los Angeles Tenants Union,簡稱LATU) 開始支持抗租行動,協助他們動員人民以及獲取法律資源。
過了九個月,他們收到僅14%的租金上調,一份在美國十分罕有的三年合同、因拒付而造成的一切罰款的取消,以及三年後能集體談判下一份合同的權利。
2018年:洛杉磯,Burlington聯盟
在拉丁裔無家者的數量暴漲底下,在一個位於洛杉磯,受迅猛的仕紳化影響的拉丁裔社區Burlington Avenue,有一個抗租行動在同一個物業裡的三棟大廈裡開始了。當房東把租戶的租金上調25-50%,192個單位中有36個公開宣告開始抗租行動。此外,大廈裡的惡劣條件也是租戶們其中一個共同的投訴。到了第二個星期,一共85個單位在抗租,單位數目接近一半。居民從抗租行動宣言開始就自我組織起來。隨後,該地=區的洛杉磯租戶聯盟以及鄰近反對驅逐的社區法律辯護組織皆向抗租者提供協助。
司法體系為了化解抗爭,將每個單位在法院程序中分開審理。一半的單位贏得判決,其餘的被迫離開。
洛杉磯歷史中最大型的抗租行動:Burlington租戶 vs 卑鄙房東律師Lisa Ehrlich
2017-2018年:多倫多,帕克代爾
在2017年,居住在屬於同一個房東的多棟大廈裡的300個單位的租戶,在多倫多的帕克代爾區舉行了一場成功的抗租行動。該社區經歷著迅猛的仕紳化,而涉事的房地產公司因為公寓條件惡劣,以及試圖通過漲價將租戶們趕走,所以在租戶們當中名聲已經很壞。
當房地產公司嘗試漲價,有些鄰里決定宣布抗租,其他人隨即迅速加入,以議會的形式組織起來。另外一個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中重要元素就是「組織帕克代爾」(Parkdale Organize),一個在2015年的另一場社區抗爭出現,但是同在帕克代爾區的租戶組織。「組織帕克代爾」協助動員群眾參與抗租行動,走訪受影響的大廈、提供資源,以及分享抗爭的眾多模範。三個月後,他們成功阻止了租金上調。
在這個例子的影響下,住在帕克代爾另一個大型的、189個單位的大廈的租戶在來年開始了抗租行動。當房地產公司命令大幅上調租金,55個單位的租戶組織了一個議會,然後開始抗租。抗租兩個月後,租戶們贏得他們的訴求,而房東亦取消了租金上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