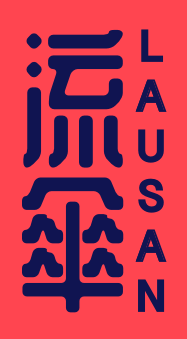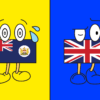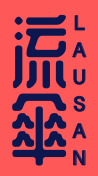譯按:原文刊於Good Men’s Project,並獲威廉與瑪麗學院亞太島民美國研究系助理教授R. Benedito Ferrão授權轉載。英文原文見此。印尼文譯本見此。詳情請聯絡流傘義務翻譯團隊。
譯者:Lillian Ngan、Yehua
這麼多年來,我在這座港口城市也不曾見過這樣的景況:圍城的香港。抵港當日適逢八月五日大罷工,傍晚五點,銅鑼灣的商店以落閘的形式來迎接我。以商業活動和不夜天聞名的城市,化成蒼涼的面孔。在時代廣場,我看見一群穿著黑色衣服的年輕男女,帶著黑色口罩,他們有些戴著頭盔,另一些則手持黑色雨傘,在天色明媚的日子充當抗議的象徵。我本能地取出手機拍照。
其中一位年輕人朝我走來,口罩遮蓋了他的聲線,問我可否避免拍攝到示威者的樣貌。我向他展示我拍到的照片:雨傘遮蔽了影像的大部分,只剩幾雙腿映襯在微弱的燈光中。
我從來未見過這樣的香港。
抗議活動萌生自去年中,香港特首林鄭月娥嘗試推動逃犯條例立法,令在港罪犯有可能被港府移交到中國受審,繞過香港的司法制度。去年九月,林鄭宣佈撤回條例,但隨著波瀾壯闊的運動開始放眼民主改革,情況已覆水難收。
2014年的雨傘革命也爭取著相似的改革,而雨傘自然是象徵該次運動的符號。兩個多月的傘運失敗告終,但僅僅五年後,示威者便再次高舉雨傘,質詢一國兩制是否已名存實亡。這問題自英國殖民時代結束以來從未獲得徹底解決。
香港是我成年後最早獨自旅行的外國城市之一。我那時21歲,移民到美國後,第一次由加州出發探望在果阿 (Goa) 的家人。
那趟在香港中轉的成長旅程永遠都在我記憶中佔有特別的位置。但它更是正值重要的歷史時刻:當時是1995年,統治了香港99年的英國將於兩年內將香港的主權移交至中國。
之後我又一次在香港中轉;這次我趁機到訪了澳門。那時是1999年,葡萄牙在澳門的租約期滿,使澳門也得回歸中國,標誌著葡萄牙在亞洲將近500年的殖民主義結束。這股浪潮也延伸至我自己的故鄉:果阿,葡屬印度的首府,在1510至1961年間被葡萄牙人所佔領。
我並非家庭中拜訪這些帶有歐洲帝國遺跡的亞洲土地的第一人。然而,在我的家人探訪這些地方之前,這些島嶼文化的影響早已是我們生活的一部分。
早我幾年遊覽香港和澳門的父親,拍攝了青花瓷的照片,使人想起我祖父母和其他果阿人家中仍然保存的陶器。
葡語語系世界連接了亞洲各地,譬如果阿、帝汶和澳門,但某些亞洲地區之間的聯繫甚至遠早於葡萄牙人的抵達之前已經形成。
我第一次去香港和澳門的旅行途中,我在當地居住的果阿家人們給了我他們朋友的電話號碼。在之後的幾年間,我學到了他們標誌性的家族人物和歷史,印證了葡亞兩地的文化與血緣。其中一位是於2016年去世的China Machado,生於1929年的她是最早享譽國際的有色模特兒之一,她有著中國、果阿和葡萄牙的血統。
印度將果阿併入國土抑止了果阿人自我解放的嘗試,使這個前葡屬印度地區成為了一個「後殖民地的殖民地」。
由於這些關聯,我總覺得香港和澳門與果阿有著相似的歷史。它們都是交織著多元文化的狹小地方,吸收和改變遠方傳來的影響,化為自身的文化。這並不是說殖民地的一切都很美好。
這幾片土地不乏政治抗爭的歷史。但一些在地的傳統和文化發展,卻始終因為當下──尤其是民族主義盛行之際──對這些歷史的重新敘述和理解而被削弱。
不同於香港和澳門,果阿被歐洲殖民者統治的收結並非出於協議。1961年十二月十九日,印度與葡國軍隊交戰兩日後,印度戰勝並重奪果阿。而雖然果阿人在殖民主義的課題上有著各式各樣的政治思想,當中亦包括支持葡方、反對葡方和親印度的陣營,但到最後,果阿人也無權選擇自己的土地解放後的前途。
印度將果阿併入國土抑止了果阿人自我解放的嘗試,使這個前葡屬印度地區成為了一個「後殖民地的殖民地」。這一切都很諷刺,尤其是印度於1947年才把英國殖民者趕走,自立成國。
去年八月,我在香港停留了一個禮拜,期間社會的情況一直都很緊張。由地鐵站內遺下的文宣和罷工時行動者各自成群可見,這次運動當中也有一些分歧。儘管抗爭者的目標一致──要挑戰北京對香港的政治箝制──卻不難看見揮動美國國旗等突兀的示威模式。
我對以美國象徵民主這一著有保留,尤其是川普為尋求2020大選競爭對手拜登的黑材料,而與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秘密通話的醜聞傳出之際。一些針對抗爭者的攻擊也說明,香港人對現時的政治情況的想法並不一致。
我看著歷史在香港展開,就像窺見平行時空裡,20世紀上半葉的果阿:人民嘗試著處理不同派別之間的矛盾,自行就殖民統治的將近結束尋找出路。
我總覺得香港和澳門與果阿有著相似的歷史。它們都是交織著多元文化的狹小地方,吸收和改變遠方傳來的影響,化為自身的文化。
我對香港的年輕人組織起來,在城市的各處也能夠聚集人數和力量的壯舉感到敬畏。
當時的果阿人又是如何傳播有關秘密會議和行動的消息?這些問題在現時果阿學生讀的歷史課本中不會找到答案,因為今天歷史教育灌輸的是一種扁平化、右傾的民族遺產。
八月十二日是我留在香港的最後一天。這天抗爭者使出了堪稱政治天才的大型示威活動:為求國際社會注目香港,他們佔領了機場。
我在香港站等侯機場快綫時,一些穿黑衣的示威者敦促我和其他旅客不要前往機場。其中一人向我解釋:他不想我在機場遇上麻煩。想到他年紀應該與我的大學學生和初來香港的我相若,我覺得很感動。
我嘗試聯絡航空公司,可是綫路繁忙;網站上仍然顯示我的航班會準時開出。乘火車很快便到了香港國際機場,面前迎來一大群和平抗爭者,他們要為一名在警察和示威者的衝突中喪失一隻眼睛的女手足討回公道。
前一天,警察在尖沙嘴對示威者發射布袋鉛彈,其中一發擊中了一個女示威者得面部,導致他失明。機場擠滿了示威者和不知所措的旅客,卻不見一個航空公司的職員。那個傍晚沒有航班可以離開香港。
我看著歷史在香港展開,就像窺見平行時空裡,20世紀上半葉的果阿:人民嘗試著處理不同派別之間的矛盾,自行就殖民統治的將近結束尋找出路。
我離開了機場,到了我朋友的家借宿。到了明天,航空公司才向我講明白我的新旅遊安排。我再次來到了機場,佔領的示威者還在,我還以為我連續兩天也去不了果阿。
正如第一次來香港的旅程一樣,我穿梭於兩個原本由歐洲殖民統治的地方。兩地人民在各自的歷史中,都經歷了被異地人主宰自己的政治前途的命運。混亂之中我離開了香港,到埗後發現之後的航班都被取消了。
過去三十年,我每次來香港都見證了它當代的重要歷史接點:主權移交前、後,還有這趟遇上的時代革命。這裡的年青人走上了最前綫,叫人注目。由年青人帶領政治運動在歷史上早有前科,當中包括五、六十年代美國的黑人民權運動。
說到由年青人領導運動的例子也不必只談歷史。現今人類最緊迫的議題──全球暖化──正是由年青一輩帶起關注和推動改變。
香港這場由年青人主導的革命除了影響不凡,還揭示著那些果阿人也經歷過的,對殖民性的掙扎。如果說這個時刻的香港是窺見過去的縫隙,那麼這場革命也許可以促使我們留意其它地區演得一樣激烈,卻沒有被給予同樣曝光率的政治運動。
2019年七月,我到訪了巴勒斯坦西岸地區城市希伯崙,認識到一個非暴力組織Youth Against Settlements的工作;他們致力抵制入侵他們家鄉的以色列定居者。話說回來,我到達香港的一天 (八月五日),正好是印度政府正式廢除鄰近果阿,一直是主權爭議地區的克什米爾邦的自治地位,任何將印度對克什米爾的政策粉飾成民主的說法也完全失去基礎。克什米爾的行動者繼續反抗侵害他們權力的行為,卻遭國際社會漠視,情況就如巴勒斯坦。
像這些地區一樣,現時在香港開展的抗爭跟殖民時期遺下的問題和後殖民主義的興起脫不了關係。我們現在見證的是一場為了香港的未來而發生的動盪。
在歷史與未來之間,香港正經歷著深刻變化的時代。香港人從抗爭中展示了自己的力量,體現出少數民族應該有權決定自己和他們身處的土地的命運,同時提醒我們在其它地方也存在類似的鬥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