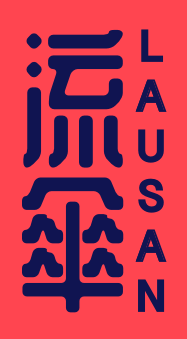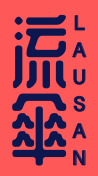本文原刊於《半島英文台》;流傘獲授權自行發布。英文原文見此。詳情請聯絡流傘義務翻譯團隊。
譯按: 女人也是人,所以本文將所有代名詞——包括「she/her」——翻譯作部首是「人」的「他」,而不使用「她」。
譯者:joisenby、Carol Wu、ZL、 yehua、T. Ho
香港——Maricel(化名)與六名同由菲律賓移徙到香港當家務工的好友趁假期去深圳一日遊。他們乘跨境巴士,來到這個以奢華的商場和發展迅速的科技行業聞名的廣東城市。
他們買了一大堆零食,在張家界大峽谷的玻璃橋上自拍了數張,並與巴士上同為家務工的乘客們拍了一張大合照。
他們這趟假日旅遊正值九九重陽節的長週末,是法定的週日休假。
當他們返回香港時,入境處職員告知他們,香港的公共鐵路系統 (港鐵) 當晚已停止運作。
隨著警察與示威者之間已經緊張的關係進一步惡化,不少地鐵站開始間歇性關閉,某一些車站甚至提早結束夜間服務。
Maricel和朋友乘巴士到達九龍後,手機信號終於恢復了,讓他們可以向僱主們解釋自己的情況,但當時已經是晚上11點。
朋友們的僱主都叮囑他們注意安全,並盡可能返回僱主的家。
但26歲的Marice要遵守僱主實施的宵禁令,而他已經遲到了近三小時。香港的《僱傭條例》規定移民家務工每星期應獲最少一天休息日;休息日的定義是連續不少於24小時的期間。根據此例,僱主無權在連續24小時的休息日完結之前,實施任何宵禁。
Maricel的僱主當下就在電話上解僱了他。他本想乘坐的士回家,卻因示威活動擾亂了交通而上不了的士,只好在朋友家過夜。
翌日,Marciel的僱主拒絕讓他進門收拾他的東西。僱主說,他會自行將Maricel的物品打包送去僱傭中心。
Maricel自2018年初就為這個家庭工作:烹飪、清潔、照顧10歲大的女兒和一隻貴賓犬。
在剝削的制度下求存
根據香港2018年的人口普查,香港一共有 386,075 名移民家務工 (移工) 。
他們過着朝不保夕的生活——據亞洲移居人士聯盟發言人和菲律賓移工Eman Villanueva所說,移工缺乏勞工保障,常被僱主過勞和短付工資。
有別於其他國家的僑民,來自東南亞的移工不能在居港滿七年後申請成為永久居民。他們沒有成為公民的合法途徑。
在香港工作了足足28年的Villanueva說:「限於政府現時的簽證制度,我們都只是臨時的移民。」
自六月起,反送中引發了「爭取民主」的示威運動,但在這大環境下,不少移工卻發現自己的處境比平時更加弱勢。
在十月初,一名年少的學生成為首個在示威期間遭警察槍傷的示威者,局勢隨之升溫。
數天後,港鐵局部暫停了運作;而港鐵正是移工在每周僅有一天的休息日裡出入往返的主要途徑。
隨著示威者與警方的衝突升級,警方越加頻繁地出動催淚彈和水炮車,使不少移工社群感到惶恐不安。
另外,亦有移工因為語言隔閡而難以具體地掌握運動的情況,尤其有關事態發展的時間和因由的準確資訊。
Basilia Mendoza,一個38歲的菲律賓籍家務工,靠Facebook和他在香港的親戚得知事態發展,但他發現社交媒體並不是準確的消息來源。
「我在這地工作,當然需要知道在發生甚麼事。但當我聽到很多不同版本的敘述,我無法分辨真假。」Mendoza說。
菲律賓和印尼政府均呼籲移工遠離示威活動發生的地方。
「我們一直勸喻我們的家務工不要前往這些地方,因為只有這樣才能確保他們不會受傷。」菲律賓海外勞工辦公室助理勞工隨員Antonio Villafuerte說。

移工是香港薪酬最低的勞動者,法定最低月薪只有港幣4630元(590美元),法例亦規定他們必須在僱主的家中留宿。僱用本地勞工的法定最低工資是時薪港幣37.5元,若以每月工作26天,每天工作10小時計算,最低月薪則為港幣9750元。這是移工可獲的最低月薪的兩倍,而大部分移工每天工作時數均多於10小時。
相比於移工,2018年香港各行業的月入中位數是港幣17500元。據入境事務處規定,僱主必需月入不少於港幣15000元方可聘請家庭傭工。
即使如此,根據一份今年三月發表的報告,移工為香港經濟貢獻了總共九百八十九億港元。
香港印尼移工協會主席Sring Atin指,移工的權益在正常情況下已經沒有甚麼保障,在示威活動期間,受到的侵犯則更嚴重。
截至去年,香港約有十六萬六千名印尼籍家務工,人數僅次於菲律賓籍家務工。
有移工曾向Atin投訴,僱主為了參與示威活動,要求他延長工時——例如要移工於自己遊行期間照顧子女,或者以保障傭工的安全為由,要求他們在法定休息日整天留在家中。
香港一直有虐待移工的案件,有的被强迫超時工作,有的遭受虐打,有的甚至收到死亡威脅。
我們想傳達的訊息是:我們身處香港,是社會的一份子,無論有沒有示威,政府都必須妥善處理連繫到我們的切身議題。
Eman Villanueva, 菲律賓移工及亞洲移居人士聯盟代言人
九月以來,香港印尼移工協會共接獲五宗虐待移工的案件,不過礙於警署關閉或要處理的求助太多而只能夠延遲報案。
社運組織者慣常和執法機關溝通的方式亦因此變得更加困難。
「我們不知道怎樣作出投訴。」Atin說。
除了示威活動對移工日常生活造成的不便,有專家和組織者表示,還有一些更宏觀的,意識形態上的議題需要我們關注。
香港亞洲家務工工會聯會組織幹事劉嘉美表示,移民家務工和示威者一樣十分關注自己與僱主和政府的關係中,「自主」如何得以體現。
無論是香港在一國兩制下的狀態,還是中國對香港的控制程度,他們都覺得這是與自己息息相關的事。
就在兩年前,當中國有意聘請菲律賓女性做家務工和英語教師的報道傳出後,不少移工對如何保障在中國工作時的權益表達憂慮,事關香港有由工會和團體組成的支援網絡,内地卻沒有。
「他們也不太清楚,有些懷疑。」劉表示。
我們的示威行動關注的不是『送中』,而是移工的權益。
Sring Atin, 香港印尼移工協會主席
有些移工團體的領袖和對運動的批評聲音表示,示威活動可能漠視或蓋過了移工的訴求,例如集會權、獲得生活工資的權利和對合理生活環境的追求。
各移工團體經常籌辦有關以上議題的遊行,也不時參與香港的社會運動;他們曾於2013年支持碼頭工人罷工,早於2005年亦參與了反世貿示威。
在追求權益的同時保障生計
於十月中,印尼移工網絡(JBMI)在印尼大使館外舉行集會,要求大使就十月初時有印尼公民在示威中被捕等謠言作出澄清。
印尼大使館隨後在社交媒體上發佈聲明,澄清他們從未收到任何有關印尼公民或移工因非法集會被捕的消息。
然而組織者不滿大使館在Facebook的貼文上只使用了印尼語,認為這樣不足以闢謠。
這場集會原定於前一個周末舉行,但礙於各區的反政府示威而只好延期。
「我們的示威行動關注的不是『送中』,而是移工的權益。」香港印尼移工協會的Atin說。他強調將兩者分清楚的重要性。

一群女士走在灣仔鵝頸街市旁的灣仔道上。這一帶有很多印尼商舖,離2019年9月30日灣仔示威發生的地方只有兩三街之隔。
一群女士走在鵝頸街市旁的灣仔道上。這一帶有很多印尼商舖,離示威發生的地方只有兩三街之隔。[Betsy Joles/Al Jazeera]
亞洲移居人士聯盟的Villanueva指,一些曾經參與這場民主運動的移工,因為害怕丟掉飯碗或者妨礙自己未來組織活動的能力而已停止了參加。
「就算是亂抛煙頭這種小事,也可隨時令我們的簽證無法續期。」Villanueva說。他和妻子與在香港出生的兩歲女兒一起居住。他的妻子亦是工會成員和移工。「如何融入這地,而又避免捲入危險,是我們要面對的挑戰。」
Maricel的僱主把他開除後,不久又作出了讓步,說他可以選擇留低繼續工作,或者提早解約。Maricel和這個家庭的合約要到二月才完結,他擔心提早解約會損害他於未來的求職機會。
「我選擇了繼續工作。」Maricel在之後透過WhatsApp告訴半島電視台時說。「為了家人,我必需這樣做。」
他指僱主以臨時沒收護照和拒絕一天休假作為懲罰。
儘管各種剝削的存在,仍有許多人相信香港的司法系統、工會組織網絡及家務工的團體令這座城市相比其他國家是一個比其他國家較為公平和美好的工作地方。
「我們想確保我們提出問題時,語調不會聽上去像是在責怪示威者,因為那並不是我們想傳遞的訊息。」Villanueva解釋。
「我們想傳達的訊息是:我們身處香港,是社會的一份子,無論有沒有示威,政府都必須妥善處理有些連繫到我們的切身議題。」